当祖国被日本侵略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位身高一米七、身材壮硕、嗓音粗重的马来西亚女华侨李月美穿上弟弟的衣服,谎称自己是个小伙子,报名参加了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成了一名军车驾驶员。 李月美的长相、性格和装扮让她看起来就是一个妥妥的“小伙子”,回国服务期间竟无人发现她是个“假小子”,真是“现代版的花木兰”。 说起来,李月美在马来西亚槟城长大时,就没把自己当姑娘家待。父亲开着家小修车铺,她打小就蹲在铺子门口看父亲修车,扳手、螺丝刀耍得比弟弟还溜。 16岁那年,弟弟偷偷学开货车,她扒着车厢跟了三趟,硬是看着学会了,趁父亲不注意,把货车开到郊外的空地上练,回来时车斗沾着草,她只说是弟弟开的,父亲骂了弟弟两句,她在旁边偷偷乐。 1939年,收音机里天天播着祖国被轰炸的消息,槟城的华侨聚在会馆里捐款捐物,有人说“光捐东西不够,得有人把物资送回去”。南侨机工招募的消息贴出来那天,李月美攥着攒了半年的工钱就去了,可报名处的人瞅着她直摇头:“姑娘家别来添乱,滇缅公路上全是悬崖,男人都未必扛得住。” 她气坏了,回家就把弟弟的粗布褂子套上,剪了齐耳短发,往脸上抹了点锅底灰,再压低嗓子说话——活脱脱一个黑壮的小伙子。第二天再去,报名的人看她“浓眉大眼”,说话瓮声瓮气,没多问就登了记,名字写的是“李月美”,没人想过这名字底下藏着女儿身。 滇缅公路的险,是真能吃人。路面坑坑洼洼,一边是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下雨天泥泞得能陷住车轮,晴天又被太阳晒得滚烫。李月美和男机工一样,开着十轮大卡车运军火,饿了啃口干粮,困了就趴在方向盘上打个盹,半个月不洗澡是常事。 有回遇到日军飞机轰炸,她猛打方向盘把车拐进山洞,炸弹在身后炸开,震得她耳朵嗡嗡响,可她顾不上捂耳朵,先爬下车检查轮胎——那车上拉的是前线急等着用的炮弹。 战友们都爱跟“他”搭伙,说“月美力气大,卸军火能顶两个人”。有次一个新兵开车掉了沟里,李月美跳进齐腰深的泥水里,和三个男机工一起把车推上来,浑身泥污地坐在路边笑,露出两排白牙。没人注意到,她夜里总找借口单独睡,换衣服时要躲到灌木丛后,来例假时肚子疼得直冒汗,还得硬撑着说“吃坏了肚子”。 身份差点暴露是在1940年冬天。她在保山运输站卸货时,被滚落的炮弹箱砸中腿,疼得晕了过去。战友把她抬到医疗站,医生要剪开裤子检查伤口,她猛地睁开眼死死拽着裤腰,脸都白了。医生急了:“都快截肢了还犟啥?” 她没办法,只说“我怕疼,让女护士来”。医疗站的护士长是个华侨大姐,掀开她的裤腿时,看见的不光是伤口,还有贴身藏着的一小块花手帕——那是母亲给她绣的,她一直带在身上。 护士长惊得捂住嘴,可看着她眼里的恳求,终究没声张,悄悄帮她处理了伤口,还塞给她一包红糖:“以后别这么拼,姑娘家身子金贵。”从那以后,护士长总找借口给她送点干净衣服,李月美知道自己被看穿了,却没退,只说“等把鬼子赶跑了,我再做回姑娘”。 直到1942年,她在一次运输中翻车伤了脊椎,躺在医院里动不了,护士给她擦身时,才发现这“小伙子”竟是女儿身。消息传开,战友们都傻了——那个总抢着干重活、笑起来震天响的“月美”,竟然是个姑娘。有人红了眼眶:“咱天天跟她称兄道弟,她却一个人扛着这么多事。” 后来李月美伤好后回了马来西亚,可滇缅公路上的机工们总念叨她。有个老机工在回忆录里写:“月美不是假小子,她是把自己活成了能为祖国挡子弹的样子。” 你说,是什么让一个华侨姑娘,甘愿藏起女儿身,在悬崖路上玩命?是收音机里同胞的哭声?是会馆里华侨的拳拳之心?还是那句“我是中国人,祖国有难,不能躲”?在那个年代,多少像李月美这样的人,把个人的安危抛在脑后,只想着“能为祖国做点啥”。 这样的“现代花木兰”,该被我们记多久?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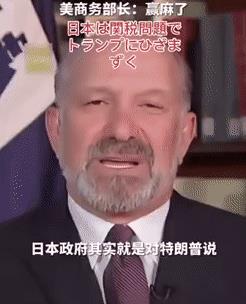




用户16xxx07
[作揖][作揖][作揖][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