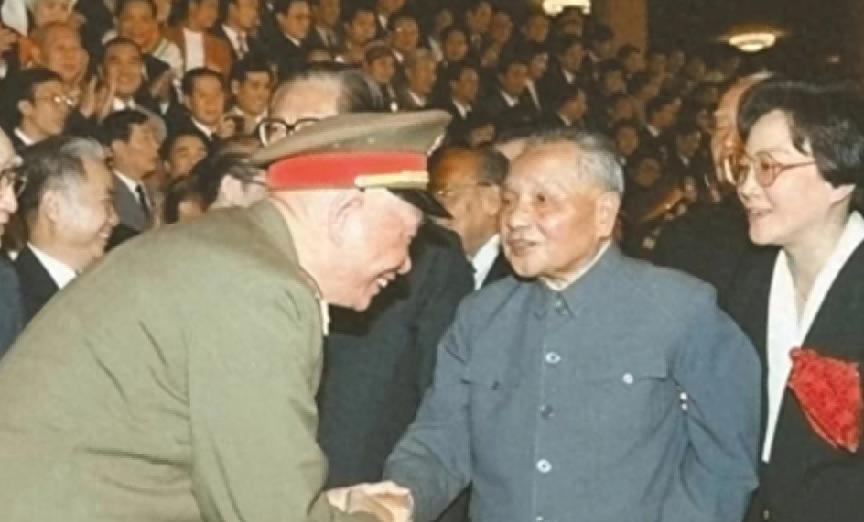1949年1月9日晚上,解放军打到了第72军军部附近。第72军副军长谭心决定投降,对部下说:“这个仗是打不下去了,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大家都是中国人,拼什么?和共军联系,不打了。” 第二天清晨,当天光刺破淮海平原上空的阴霾,战场上罕见地没有响起枪炮声。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伏的集合号。一万四千名国民党第72军的官兵,在河南永城陈官庄地区,集体放下了武器。 没有激烈的战斗,没有最后的冲锋,这场规模浩大的投诚,平静得近乎诡异。士兵们将步枪、机枪、迫击炮堆积在路边,他们卸下压在身上多年的沉重包袱。 一个年轻的士兵,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信纸,那是他姐姐寄来的,上面只写着一句话:“狗蛋,活着回来就行。”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小心翼翼地折好,重新揣回怀里。 这个决定,对于副军长谭心而言,不是一时冲动,而是被现实压垮后的必然选择。军长余锦源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他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默许。 早在几天前,陈毅、粟裕联名写给他的劝降信就已经送达,信中的话语字字诛心:“贵军如欲为蒋独夫作无谓之牺牲,不仅将遗万世之羞,抑且有负父老乡亲之望。” 72军本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川军部队。这支军队的前身,在1938年于四川万县重组后,便千里迢迢开赴前线。他们是穿着草鞋、拿着中正式的川中子弟,在武汉会战的外围死战不退,在三次长沙会战中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军的铁蹄。 尤其是在1943年的常德会战中,他们作为增援部队,硬是从日军的包围圈里撕开一道口子,收复了那座几乎被打成废墟的城市。那时候,他们为保家卫国而战,每一个牺牲都重于泰山。 然而,抗战胜利的喜悦并未持续多久。内战的烽火,将这支部队彻底拖入了泥潭。 1947年,在山东泰安,整编72师被解放军重创,师长杨文泉被俘。部队在济宁重建后,士兵的成分变得更加复杂,老兵凋零,新兵脸上满是稚气与茫然。 他们从保家卫国的英雄,变成了剿匪的工具。曾经同仇敌忾的信念,被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现实撕得粉碎。 到了淮海战役,这种迷茫与绝望达到了顶点。杜聿明集团被围困在陈官庄,天寒地冻,粮弹断绝。士兵们几天吃不上一顿热饭,伤员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哀嚎。 空投的物资杯水车薪,而且大部分落到了我军的阵地上。72军的官兵们心里都清楚,徐州是回不去了,援兵是看不见了,坚守待援的命令,不过是一张催命符。 更让他们军心动摇的,是对面阵地传来的攻心战。那些带着浓重乡音的喊话,不是在打仗,而是在拉家常。 “对面的川军兄弟们,我们司令员也是四川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的家人在盼着你们回家过年!”这些话语,伴随着《孟姜女》的悲凉曲调,在寒冷的冬夜里飘过阵地,钻进每个士兵的心里。 事实上,早在战役开始前,我军的情报工作就已经细致到了惊人的地步。华野敌工部不只掌握了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甚至对每个高级将领的个人特征、性格习惯都了如指掌。 他们知道72军军长余锦源好赌博、饮酒,善剃光头,也知道副军长邓军林稍矮,胖子,走路两手一晃一晃的。这种知彼知己,使得战场的主动权从一开始就牢牢掌握在我军手中。 因此,当谭心做出投诚决定时,这既是战场上的无奈之举,也是人心向背的必然结果。他们与我军派来的代表进行了火线谈判,提出了两个特殊的条件。 对外宣称72军是被歼灭,而非投诚,以保护他们在国统区的家属免遭迫害。对愿意回家的军官,予以方便。 我军方面对此表示了极大的诚意,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只要求假打20分钟,以应对国民党上峰。 就这样,一场本该血流成河的攻坚战,以一种近乎和平的方式落下了帷幕。这是1.4万名士兵的幸存,更是战争天平上,人性的重量压倒了愚忠的又一次明证。 人民早已厌倦了战争,渴望和平。这种愿望,在士兵心中,在家书里,在每一个辗转反侧的寒夜里,汇聚成了不可阻挡的力量。 谭心不是什么传奇名将,他只是在历史的关口,做出了一个符合人心的选择。这个选择让那些曾为国流血的川军子弟,最终没有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之下。 而这支72军的番号,在几个月后于川南重建,由我党秘密党员郭汝瑰接任军长,并最终在宜宾率部起义,为四川的和平解放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MCN双量进阶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