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切尔诺贝利是庄肃的,此时,有三名工作人员身穿隔离服站在入口处,他们是勇士,因为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任务,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以甘愿牺牲自我为代价,保护成千上万的黎民,他们目光坚定,随时做好了为国奉献的准备,缓缓地,拉开了切尔诺贝利的入口大门... 清晨,切尔诺贝利四号反应堆废墟深处,三道被厚重铅服裹成笨拙轮廓的人影,正挪向那扇仿佛地狱入口的阀门间大门,强辐射警报器尖鸣不止,像垂死野兽的最后哀嚎,他们每一步都踏在看不见却足以蚀骨销魂的死亡浓雾里。 领头的是核电站值班长阿列克谢·阿纳年科,他步子沉重,却异常坚定,身后是两位工程师——瓦列里·别斯帕罗夫和鲍里斯·巴拉诺夫,三人之间没有多余言语,只有铅靴摩擦地面沉重的刮擦声,以及彼此粗重的呼吸在面罩里回荡。 “阿列克谢,”巴拉诺夫的声音透过面罩,有些发闷,“这次进去,我们就回不来了,”阿纳年科没有回头,只是用力握紧了手中那串冰凉的钥匙:“鲍里斯,瓦列里,回不来也得去开那几道该死的阀门。 底下那池子水再排不出去,熔穿的水泥板下面是基辅几百万人的水源。整个欧洲……都悬着,”几天前那场惊天爆炸,撕裂了反应堆心脏,堆芯熔融物如熔岩地狱般缓缓下沉。 下方,是数千吨冷却水汇成的巨大水池,一旦高温熔岩触水,便是足以颠覆欧洲的二次蒸汽大爆炸,唯一阻止这灭顶之灾的渺茫生机,竟沉在反应堆底部那间已被高辐射彻底吞噬的地下室,手动开启排水阀门。 这任务不是命令,是招募志愿者,明知那地下室的辐射强度足以让血肉在几分钟内消融,明知踏入即永诀。 别斯帕罗夫忽然轻声开口:“昨晚……我隔着电话线,听见我小女儿哭了,” 这话像一块沉重的石头,砸进三人间短暂的沉默里,没人追问为什么哭,也没人再说什么,面罩之下,只有无声的咬紧牙关与更沉重的脚步。 那扇通往地狱核心的门就在眼前了,阿纳年科的手有些抖,钥匙几次没能插进锁孔,他深吸一口气,最后一下,终于拧动了它,铰链发出令人牙酸的呻吟,仿佛地狱张开了嘴。 门内,幽深通道被应急灯染成诡异的蓝绿色,空气里弥漫着金属与尘埃被强辐射炙烤后的焦糊味,三人相视一眼,那目光里没有恐惧的游移,只有磐石般的承担。 阿纳年科第一个迈了进去,别斯帕罗夫紧随其后,巴拉诺夫最后踏入,反手,将那扇沉重的门在身后带上,隔绝了外面微弱的光,也隔绝了生的世界。 他们在强辐射的泥沼中跋涉,每一步都是生命倒计时,目标阀门深埋于迷宫般的地下管道深处,凭借阿纳年科脑中刻下的唯一地图,三人沉默协作,终于摸到那冰冷巨大的阀门轮盘。 铅手套异常笨拙,轮盘纹丝不动,别斯帕罗夫和巴拉诺夫用尽全身力气抵住阿纳年科的后背,三人如雕塑般凝固在黑暗中,与那钢铁怪物角力。时间被强辐射拉长、扭曲,每一秒都是对血肉的无情侵蚀。 不知过去多久,一声沉闷的、仿佛来自大地深处的“咔哒”声,终于穿透了面罩,轮盘动了! 当最后一道阀门被彻底打开,地下室深处传来水流急速涌动的沉闷轰鸣。 那声音对三人而言,胜过世间一切乐章,任务完成了,他们瘫坐在冰冷的地上,强辐射带来的剧痛和灼热感开始啃噬每一寸神经。 巴拉诺夫在面罩里艰难地喘息着,低声说:“水流声……真好听,” 阿纳年科靠在冰冷的管道壁上,疲惫地点头,别斯帕罗夫闭着眼,仿佛在倾听那救赎的水声,又仿佛在倾听遥远的、再也无法触碰的女儿的哭声。 几小时后,当救援人员冒险打开那扇门,只找到三具已无生息的躯体,他们蜷缩在冰冷的管道旁,姿态却无丝毫挣扎,如沉眠于完成了最后使命的平静之中。 正是这三人用血肉之躯换来的宝贵水流声,最终阻止了那场悬在欧洲头顶的二次灾难浩劫。 切尔诺贝利的阴霾终会散去,但有些身影却永远凝固在人类记忆深处。 当阿纳年科拧动钥匙、别斯帕罗夫听见女儿哭泣、巴拉诺夫说出“水流声真好听”的那一刻,一种近乎神性的凡人勇毅便已刺破辐射阴云,照彻人间。 那扇地狱之门隔绝了生,却无法吞噬他们以生命点亮的火种,历史不会为无名者立传,却永远记得有人曾以凡胎,抵住了深渊的倾塌。 切尔诺贝利事故 来源:百度百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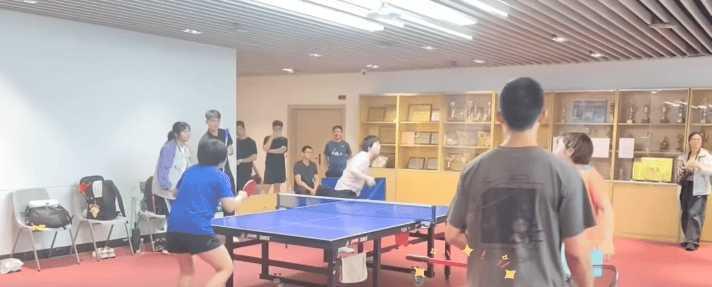



用户12xxx79
甘愿以个体的牺牲奉献换取整体的利益,是生命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