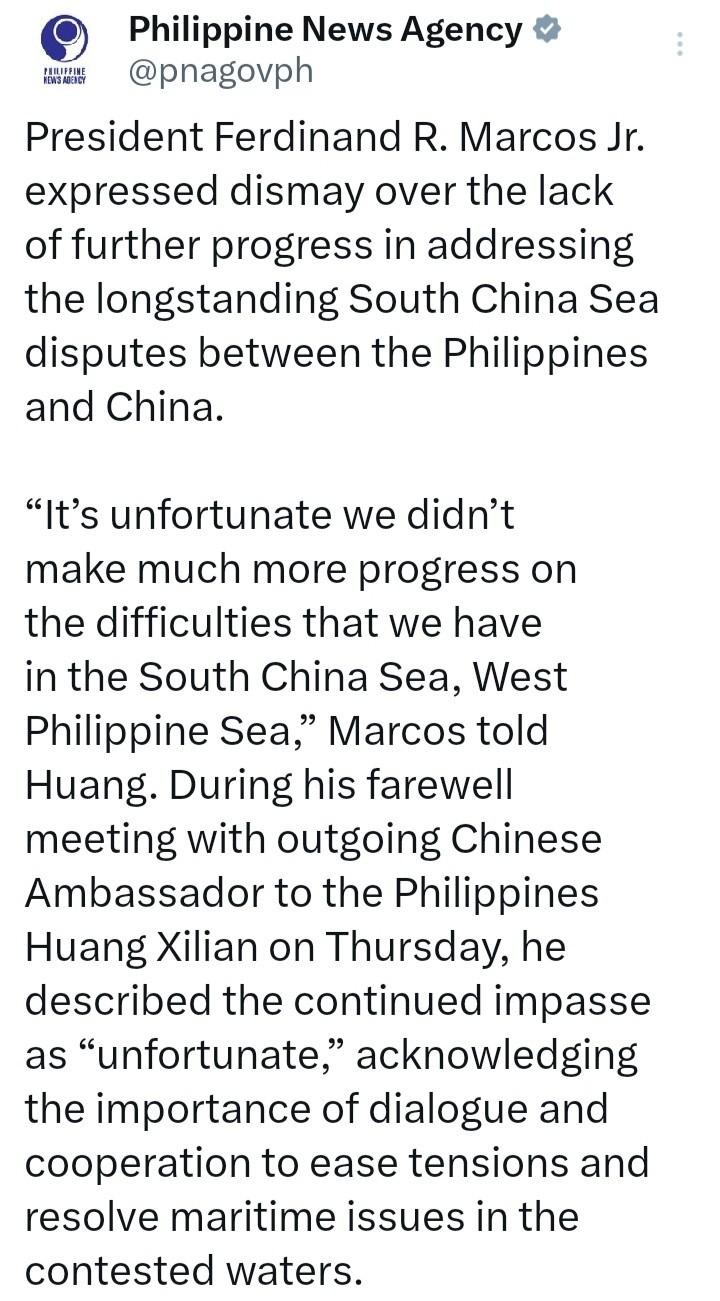1979年我国女翻译刘禄曾前往美国进行访问无意间她发现一个美国男人一直盯着自己看,几分钟后这个美国男人竟然情绪激动的直接冲到了她的面前,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1979年的南京春寒料峭,刘禄曾刚从一次长途飞行中回来,脸上带着旅途的疲惫,却掩不住眼神里的光,几十年来,她的生活像一条被战争搅动过的河流,时而激荡,时而沉静,但总在往前流。 那年她五十岁出头,刚结束一次外事访问任务,飞机降落前,她把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看了一遍又一遍,那本笔记本她从来没有借给任何人看过,纸页已经泛黄,边角也起了毛边,每一页都写着密密麻麻的英文单词、军衔代号、心理分析和审讯提纲,这些内容,她年轻时用铅笔在坑道里一点点写下,一边写一边听着炮火,那时候,她是志愿军政治部敌工部的一员,负责与美军战俘沟通、审讯、做思想工作。 她本不该出现在那样的地方,父亲是银行高管,母亲讲究门第出身,从小到大,她都穿着干净的洋装,弹钢琴、说英语,是中西女校里最出挑的女生,大学读的是法律,东吴大学的法律系,那是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女学生能进的地方,可她从不满足于只是背法条抄判例,总觉得语言和法律都该有更大的用处,她逼着自己学口音、练发音,常常一个人对着镜子说话,直到自己听不出毛病为止。 1950年冬,朝鲜战事爆发,学校里贴出动员志愿的公告,她没有犹豫,填表、体检、交代家人,动作一气呵成,那年她22岁,主动申请随敌工部前往前线,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穿军装、住地窝子、吃粗粮、走山路,甚至可能面对死亡,但她没有退缩。 火车从南京出发,颠簸几天几夜到了部队集结地,她的第一个任务,是配合审讯一批刚被俘的美军战士,当时她才到前线不久,冻得嘴唇发紫,棉鞋里塞着干草,敌工部的审讯室设在一座临时搭建的地堡里,墙壁是泥土和石头砌成的,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她把自己的笔记本塞在军服内衣口袋最靠近心口的地方,就像带着一块护身符。 战俘中有个年轻人,叫詹姆斯,是个不太合群的美国兵,他不合群的方式不是吵闹,而是不说话,初来时,他总是低着头,帽檐压得很低,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不肯看人,那年他才19岁,刚到战场就被俘虏,身上带着几道浅浅的伤口,眼神始终飘忽,刘禄曾负责给他做心理引导,她没有直接问问题,而是从他的家乡、他喜欢的球队、美国的节日讲起,她甚至从后勤处找来几页被战火烧焦边角的旧《生活》杂志,指着上面的照片让他认人,詹姆斯看着其中一张女人抱着孩子的照片,眼圈红了,那是他母亲,照片是美军宣传材料的一部分,被意外收录进了审讯资料,刘禄曾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把照片递给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收好。 那年圣诞节,敌工部安排了一场特殊的广播行动,刘禄曾被调到前沿广播点,负责用英语向美军喊话,坑道外是雪地,坑道内是黑暗、潮湿和闷热,她用一台老旧的留声机播放美国民歌,有时亲自用手摇喇叭喊话,那些声音穿过风雪,传到对面阵地,不知道有没有被谁听到,但她知道自己得做这些事,不是为了战术得分,而是为了让一些人知道,他们还活着,还有人记得他们。 广播结束后,她回到战俘营,偷偷在几名战俘床边留下了纸条,纸条上写着“圣诞快乐”“你妈妈希望你活着回家”“我们希望和平”,这些纸条上没有署名,但每一张都写得认真,字迹工整。 詹姆斯收到的那张上写着:“谢谢你的善意,”他用铅笔在背后写下自己的名字和日期,那张纸条他一直留着,折了几次,边角都磨破了,1979年,他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门口等到了那个他以为再也见不到的人,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沉默寡言的俘虏,而是华尔街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带着那张纸,走到刘禄曾面前,没有说太多,只是递过去。 重逢发生得非常突然,周围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站在她面前,那一刻,没有人发问,也没有人解释,他们什么都没说,但什么都明白了。 后来,詹姆斯请全体代表团参观了他的律所,他带他们参观办公室,指着墙上一张中国地图说:“这是我从前战斗过的地方,”那天他特地穿了深色西装,把那张纸装在胸前口袋里,一路没拿出来,但手一直贴着。 几年后,他和妻子一起飞到南京,带着孩子,那次他们在玄武湖边下棋,孩子在一旁玩耍,他和刘禄曾一边落子一边讲着各自的生活,詹姆斯告诉她,他回国后学了中文,还给三个孩子起了中文名字,那一盘棋下了很久,没有胜负,也没人关心输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