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大学教授何家庆深入西南大山考察。饥肠辘辘的他,不得已向一户村民求助食物。那家汉子沉默片刻,转身端来一碗浑浊的糊状物,气味刺鼻——分明是刚拌好的猪食。何家庆看着碗,又看看村民窘迫而麻木的脸,没有一丝怒意。他默默接过来,泪水无声滑落,就着那难以形容的味道,大口大口吞咽下去。 温热的液体混着粗粝的糠麸滑过喉咙,灼烧感直抵胃袋。何家庆的眼泪不是因为屈辱,而是眼前景象刺痛了他:村民家徒四壁,灶台冷清,那碗猪食恐怕已是这家人能拿出的、仅有的“余粮”。他想起自己幼年,父亲拉板车累弯了腰,家里揭不开锅时,邻居也曾偷偷塞过半块杂粮饼子。 端着空碗的手在微微发抖。汉子和他身后怯生生的女人孩子都愣住了,他们原本带着一丝试探和麻木,甚至等着看城里“大人物”的愤怒。何家庆抹了把脸,声音有些沙哑:“老乡,家里……就靠这个?”汉子黝黑的脸上掠过羞愧,嗫嚅道:“山里地薄,打的粮……不够人吃,猪也瘦。您是城里来的先生,我们……” “我不是先生,是教人种地的。”何家庆打断他,从磨损的帆布包里掏出皱巴巴的笔记本和几小包种子,“带我去看看你们的地,还有猪圈。”接下来的几天,何家庆没走。他跟着汉子爬坡下地,仔细察看贫瘠的山地土壤和稀疏的庄稼。他发现村民习惯将猪圈建在低洼处,又脏又潮,猪长得慢还易病。更糟的是,他们用一种叫“水麻”的野草喂猪,这东西猪吃了光长膘不结实。 “试试这个。”何家庆拿出一种叫“构树”的种子,示范如何快速育苗,“这种树长得快,叶子猪爱吃,营养好,山坡石缝都能种。”他又指导汉子把猪圈挪到向阳坡地,用干草垫圈保持干燥。他指着山涧旁疯长的魔芋:“这东西,根块磨成粉能卖钱,叶子也能喂猪,比水麻强百倍。” 起初村民将信将疑,但看这教授饿得啃干饼,还肯吃猪食,不像骗人。汉子家最先照做。几个月后,何家庆结束考察绕回这个寨子。汉子家的猪圈干干净净,几头猪明显壮实了,山坡上新栽的构树苗已窜起一尺高。汉子激动地拉着他去看屋后一小片魔芋地,绿油油的长势喜人。“何老师!猪肯吃构树叶,长得快!魔芋也有人来问价了!”他媳妇端出一碗热腾腾的玉米糊,里面特意加了点腊肉丁,不再是浑浊的猪食。 何家庆接过碗,鼻子又酸了。这次不是苦涩,是希望的味道。他走遍了附近十几个寨子,把构树种植、简易猪圈改造和魔芋栽培的点子传开。他用自己微薄的积蓄买了些优质种子分发。几年后,这片曾经靠猪食待客的穷山沟,构树成林,魔芋成片,成了小有名气的生态猪和魔芋粉产地。村民们盖起了新房,孩子们背上了新书包。他们常念叨:“多亏了那年饿得吃猪食的何老师。”而何家庆,只是默默地把这些成功的经验记在本子上,又走向下一个需要他的穷乡僻壤。他始终记得,一碗猪食的重量,那是他必须用一生去偿还的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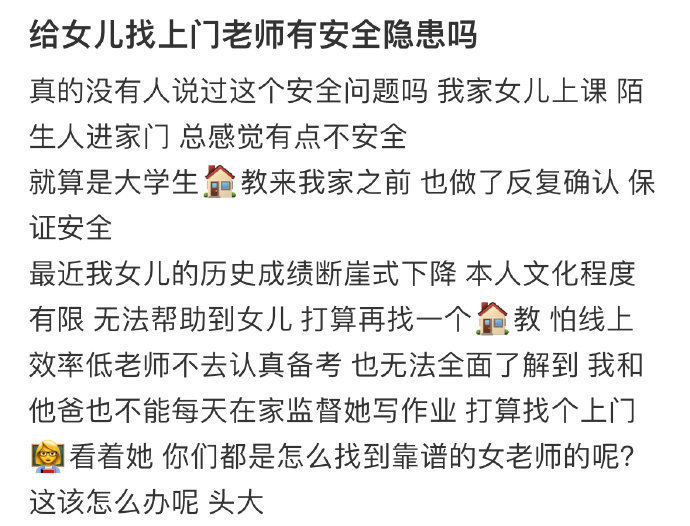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