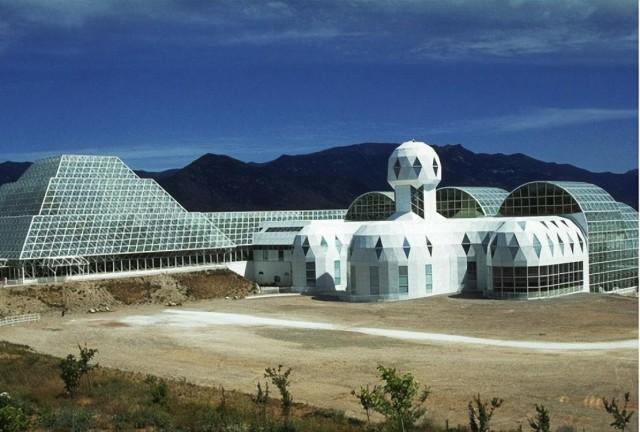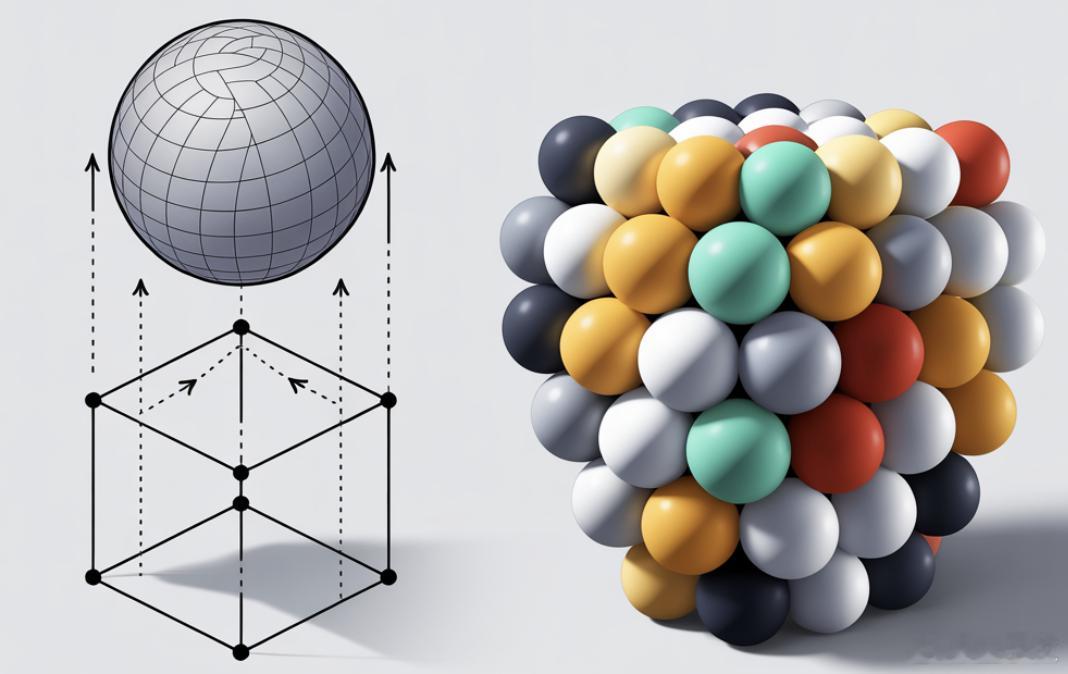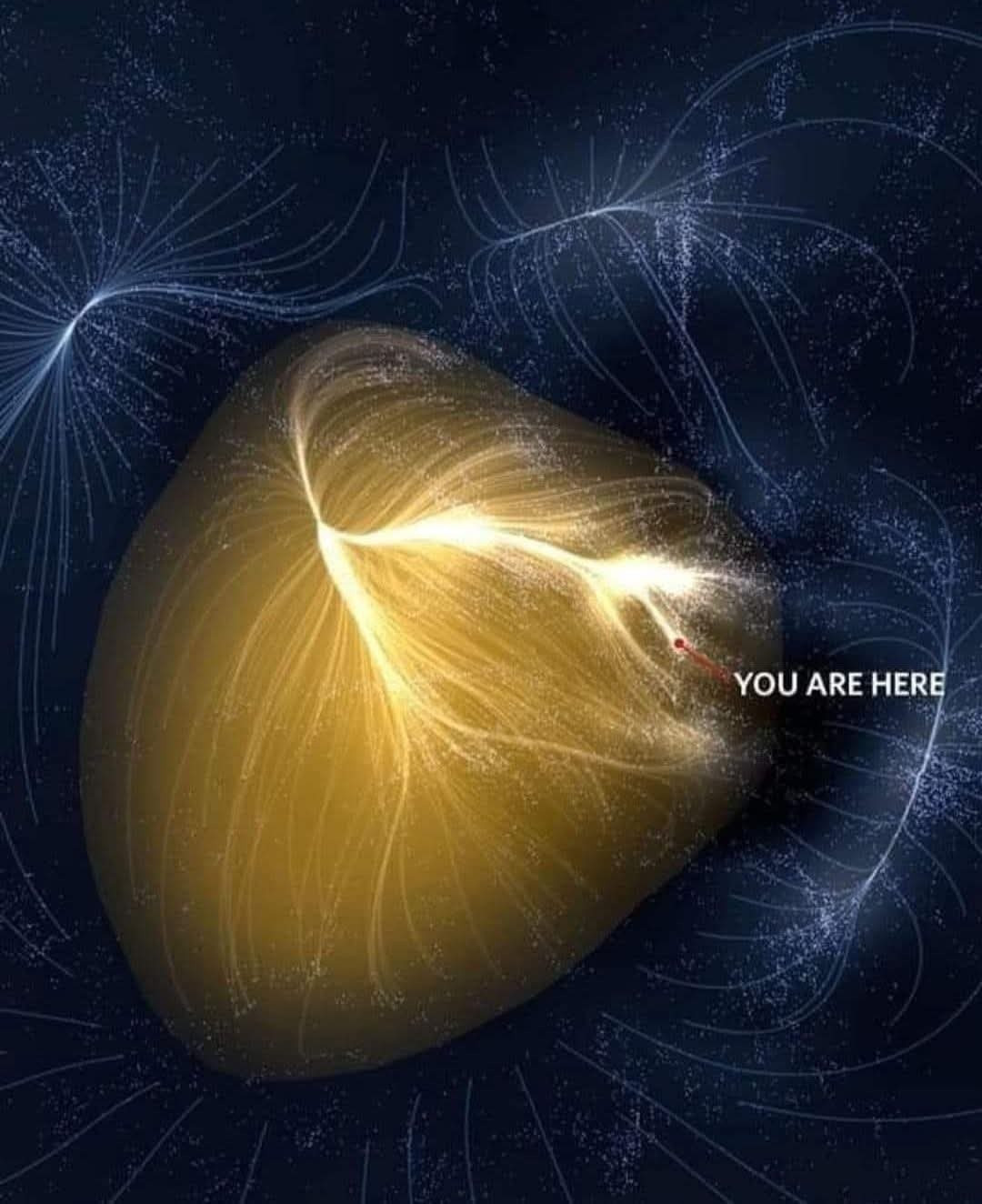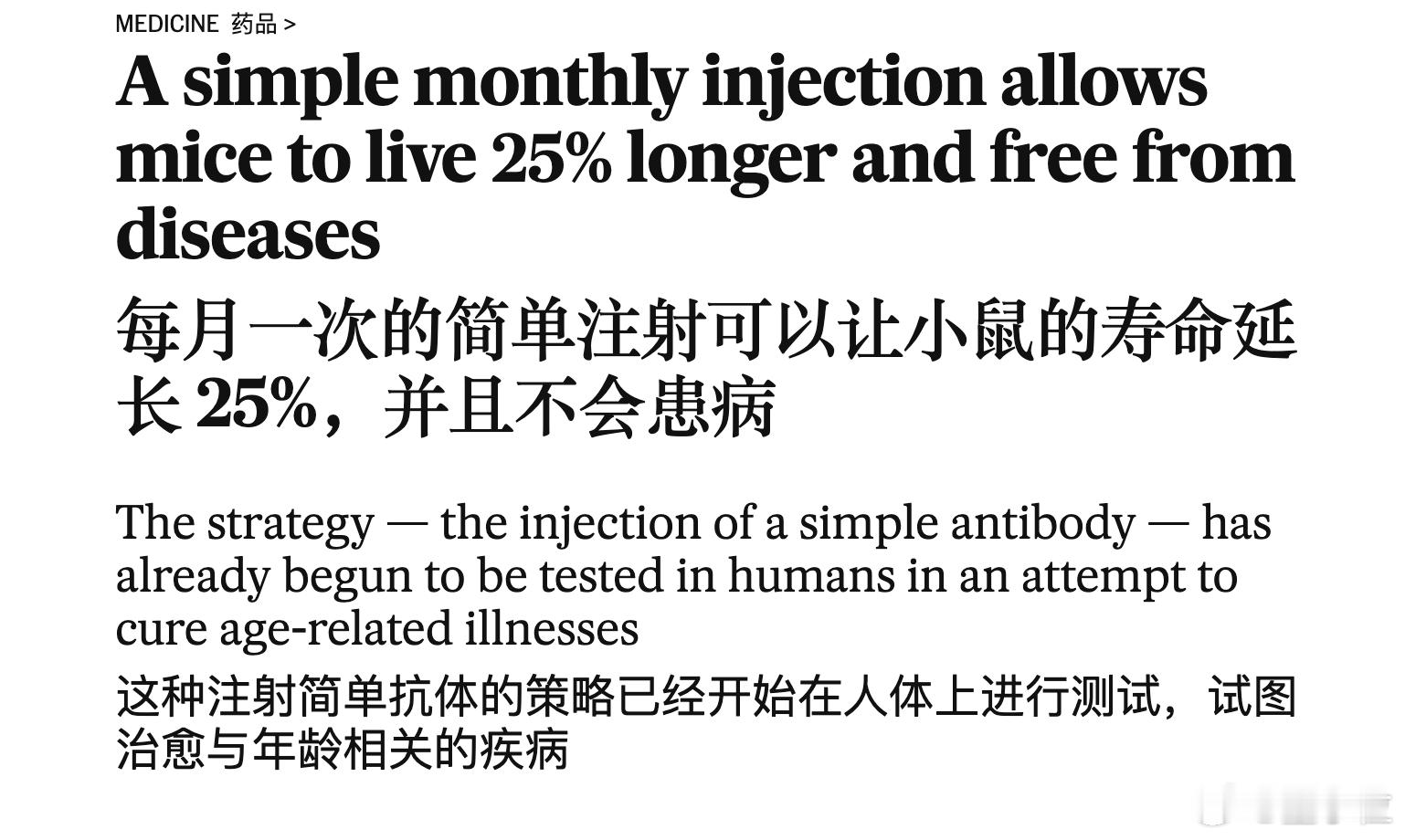1921年11月,弗莱明在实验过程中,不小心打了个喷嚏,一点鼻腔粘液刚好滴在培养基上,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这个举动,竟然帮助科学家研究出了一种药物,在70年内救了上亿人性命,人类寿命也平均提高15年。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21年11月的一天,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正在进行着日常的实验,依旧是他熟悉的琼脂培养基、显微镜和一排排等待观察的培养皿。 这天他正患着感冒,鼻塞头晕,却仍坚持照看那些细菌的生长状况,就在他靠近一个培养皿的时候,控制不住地打了一个喷嚏,一点鼻腔分泌物不偏不倚地落在了琼脂表面。 那一刻弗莱明并没有立即处理这个污染了的培养皿,只是将它放到一边,准备过后再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细小的举动会成为现代医学历史上的关键转折点。 20世纪初,尽管医学界已经明确细菌是许多传染病的元凶,但真正有效的治疗手段依然匮乏,当时普遍使用的治疗方法主要依靠毒性强烈的化学药物,例如砒霜或汞类物质,它们对细菌确实有一定抑制作用,却往往也严重伤害患者自身组织。 在战争期间,这一局限表现得尤为明显,无数士兵在战场上因为伤口感染丧命,而非直接死于战伤本身。 一战结束后不久,弗莱明带着对这些悲剧的深切记忆,回到研究岗位,立志要寻找一种能有选择性杀菌而不伤害人体的物质,他把大量时间投入在各种细菌和人体分泌物的研究中,试图揭开自然界中是否存在某种天然抗菌机制的谜团。 那一滴意外滴落的鼻涕并未立刻引起他的注意,直到两周之后,在清理实验器具时,他再次拿起那个原本被污染的培养皿,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在鼻腔粘液接触的区域,原本密布的细菌竟然大面积溶解消失,琼脂变得异常清澈。 他小心地将这一现象记录下来,进一步提取那个区域的物质,并最终确认其中存在一种能破坏细菌细胞壁的天然酶,他将其命名为“溶菌酶”。 经过多次实验,弗莱明发现它对某些细菌确有抑制作用,但抗菌谱非常有限,难以广泛应用于治疗,尽管略感失望,他并未因此放弃研究,而是继续深化对葡萄球菌等致病菌的探索。 1928年夏天,伦敦经历了一段反常的闷热天气。弗莱明在离开实验室度假之前,随意将一些培养皿放在窗边,数日后天气骤降,空气潮湿,一些漂浮的霉菌孢子悄然落入其中,等他返回实验室时,几只培养皿已经被一种绿色霉菌占据。 本是应该丢弃的污染样本,却被他注意到一个极不寻常的现象,在霉菌斑块的周围,一圈细菌被“吃掉”,形成清晰的无菌区。 他立刻开展一系列验证,成功将霉菌中释放的物质提取出来,并命名为“青霉素”,实验表明,这种物质对多种致病菌具有强烈的抑制作用,而且对人体细胞基本无害,遗憾的是,当时的技术手段尚无法大规模提纯青霉素,使得它难以进入临床应用。 直到十余年后,牛津大学的病理学家霍华德·弗洛里和化学家恩斯特·钱恩重新阅读了弗莱明的研究,并深感其潜力,他们组建研究团队,攻坚提纯技术。 通过反复试验,他们采用冷冻干燥等方法,最终获得了稳定纯净的青霉素样品,在动物实验成功后,1941年,他们将其首次用于一位严重感染的病人身上,取得了积极的疗效。 此后青霉素的重要性迅速被政府与制药企业所认识,在二战的战场上,它成为抢救伤员的核心药物之一,随着生产工艺的完善,它逐渐进入全球医疗体系,对肺炎、脑膜炎、败血症等疾病的治疗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据统计,青霉素在问世后的70年间,挽救了超过上亿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它带动了整个抗生素家族的发展,彻底改写了人类与细菌之间的战争方式,使得平均寿命提升了十余年。 1945年,弗莱明、弗洛里与钱恩因青霉素的贡献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份荣誉不仅属于他们,也属于所有曾在细菌肆虐中挣扎的人类。 谁能想到,一滴鼻涕改变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寿命轨迹,科学的伟大之处,或许就隐藏在每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之中。 信源:长江日报——“大自然创造了青霉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