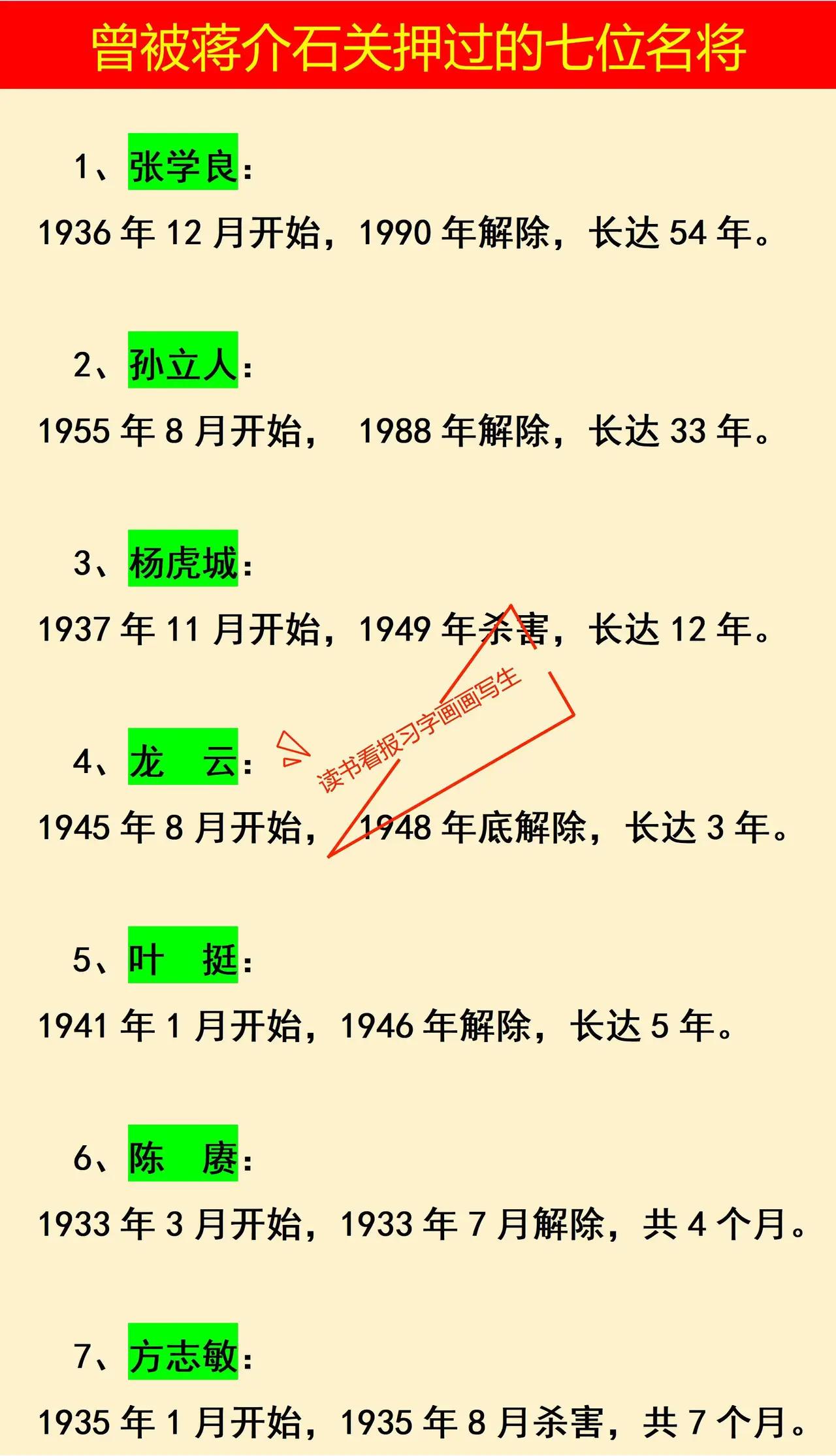1954年毛主席见到族侄,得知时任湘潭县委书记名字后:他当得了吗 “1954年10月12日上午八点半,中南海门口来人了?”警卫员小声提醒,同事点点头。那位身材敦实、脸晒得黝黑的湖南干部便是毛特夫,此刻他有些局促地理着衣角,却掩不住眼里的期待。 能进京学习,对多数地方干部已是莫大荣誉;对于毛特夫,更像一次回到长辈身边的探亲。自1927年父亲毛新梅在砚池坪牺牲后,二十八年风雨过去,他与“三叔”毛泽东再未谋面。今日相逢,既是亲情,也是组织上的关怀。 毛新梅当年在韶山主持夜校,常把半截粉笔揣进衣袖,教贫苦农民认字。毛泽东离家外出时,常收到六哥夹着草药味的信——“兄长在外保重,乡里事无多忧”。谁料到“大革命”风暴骤起,新梅在铡刀前毅然高呼“革命必胜”。那天起,毛特夫背上有了沉甸甸的嘱托。 韶山的山路陡,十八岁的他踩着露水偷偷去天津时,母亲沈绍华只塞给他一句话:“听三叔的。”在北方,他学会刻印章、写传单、带路穿过黑夜。新中国成立后,湘潭需要熟悉基层、又懂政工的干部,他被推到前台,从合作社到副县长,一步也不轻松。 9月初,湖南省委点名送他到中央政法干校深造。刚到学校,他就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口气仍是家书:“三叔,我来北京了,想向您请安。”没想到信发出第三天,车就停在干校门口。司机只说一句:“毛主席请您过去。” 丰泽园客厅里摆着土产花生、辣酱,一旁还放着一壶湘茶。毛泽东步子不急不缓,先同乡亲们一一握手,最后才看向毛特夫:“德武,长高了。”一句话,让客厅的距离瞬间拉近。毛特夫赶紧答:“三叔,母亲托我问您安。”毛泽东点头,又让人递烟,语气平常却句句关心:“冬天难过,记得替你娘备暖炉。” 席间话题从韶山桥修得牢不牢,说到湘潭县一年收了多少谷子。半盏茶工夫,毛泽东忽然问:“县里书记是谁?”听到“毛华初”三个字,他扬眉一笑又略带狐疑:“他当得了吗?”口气像兄长审视晚辈,又像最高领导权衡一县大局。 这位“华初”并非普通干部。生母罗醒牺牲后,他跟着王淑兰在白区打游击。放牛砍柴、躲追捕,练出一副硬骨头。1938年,17岁的他走进延安窑洞。毛泽东听他提出“想要匹马去前线”,严肃指出“公家的牲口动不得”,然后从稿费里掏出三万边币:“拿钱坐车,总得合法。”那晚,华初悄悄把钱压在枕头下,第二天全数交给组织,只留两张买干粮。 东北、松江、湘潭——战争与建设把他推着往前走。1952年,他顶着28岁稚气的脸,当上湘潭县委书记。口音仍然浓重,衣服常常补丁连补丁,可干部谈起他,总说一句“心里有杆秤”。 毛特夫对毛泽东说:“三叔,他能行。”这一句不是恭维,是长期搭班子的体会——凡是征粮、修水渠、分田土,只要有华初坐镇,干部和群众吵得再凶,夜里也能达成笔头协议。毛泽东放下茶杯:“好,年轻人就该挑担子。”他抬手示意身边秘书记录,声音放得很低,却透着笃定。 时间跳到1955年12月。干校毕业典礼前夕,毛特夫再次获准进丰泽园。客厅里除老乡外,还来了刘少奇和周恩来。毛泽东给大家夹一道扣肉,说是韶山做法,肥而不腻。酒过三巡,他突然问:“德武,留下来不?”毛特夫放慢语速:“家里选我当县长,我得回去。母亲年纪大,也得人照顾。” 毛泽东轻轻嗯了一声,似乎早有预料。他提醒:“回去后,别光忙公事。学政法的,得让法律为农民说话。”毛特夫点头,心里记下一笔。那年冬末,他回湘潭正式履职。六个月后,全县第一部以县政府名义发布的农田水利条例出台;两年内,湘江两岸堤坝全部加固,告别“春汛必抢险”的窘境。 再往后,毛华初调往省里主持工业口工作,毛特夫也因实绩被提拔。韶山那片山岭上,乡亲们仍把两位“毛县长”的轶事当成茶余谈资:一个脾气急,一把抓;一个说话慢,步子稳。正是这急与稳,让新中国最初的基层治理有了温度,也有了厚度。 今天读到那句“他当得了吗”,不难会心一笑。领导的疑问,是试探,更是期许;而回答的底气,则来自日日奔走在田埂上的双脚。毛特夫与毛华初,一个执政法之笔,一个握组织之舵,他们用不同方式,补上了烈士父辈未竟的那段短缺。历史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在湘潭留下了最朴素的注脚——干部能不能当,全看是否心里装着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