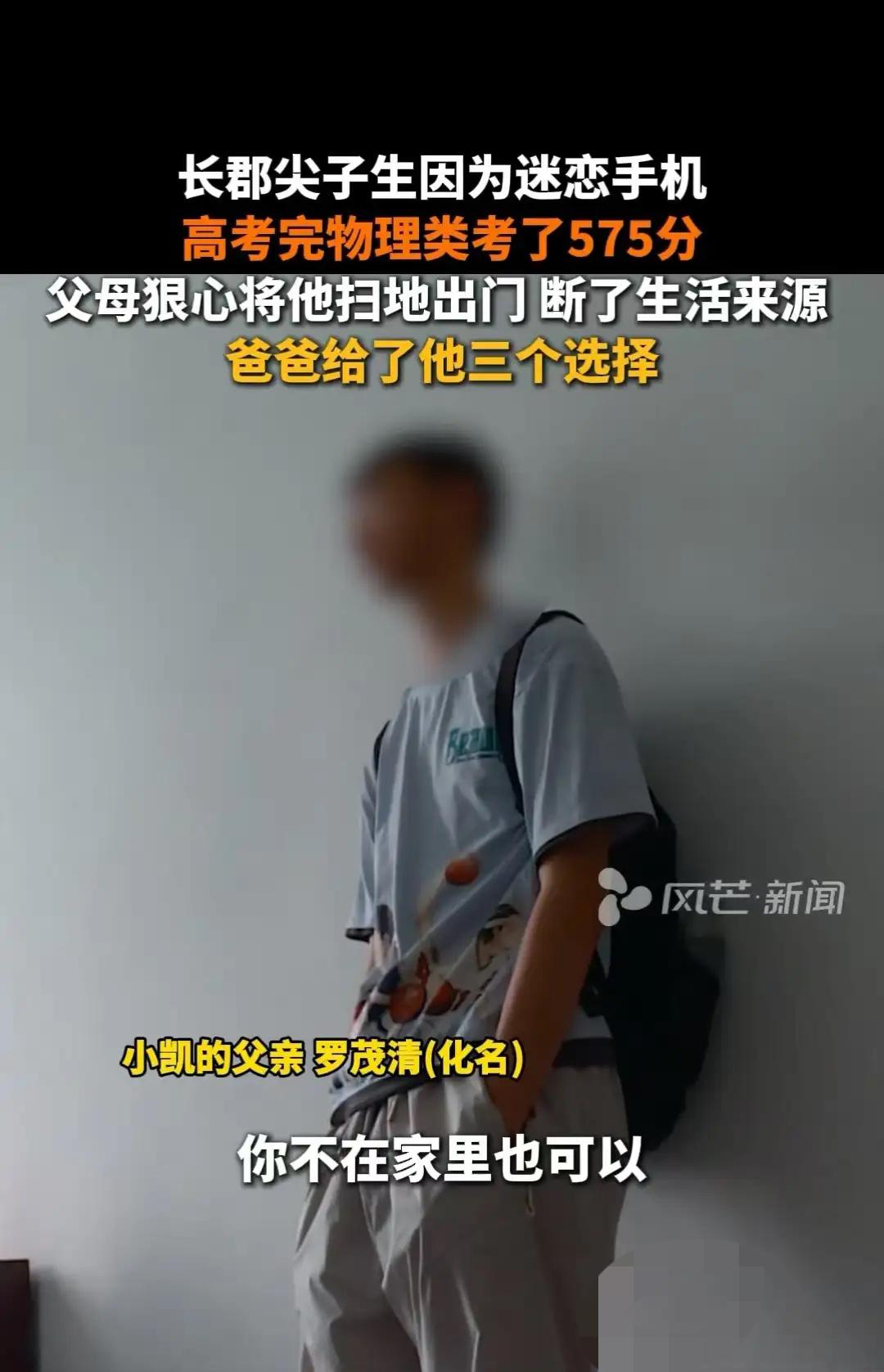湖南,男子高考考了575分,离父母要求的985、211院校相差甚远,被父母扫地出门并断了生活来源。男子找到调解员,父母依然表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给了他两条路,要么复读,要么出门打工。 湖南长沙的夏天,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小凯站在派出所调解室门口,攥着衣角的手沁出汗——他怎么也没想到,高考后575分的成绩单,会把自己从家“推”到这扇门前。 三年前,小凯攥着长郡中学录取通知书,父亲罗茂清在工地扛钢筋的手,把通知书摸得起了毛边:“我娃是尖子生,将来肯定考985!” 那时的小凯,书包里装着满分试卷,眼里有光,走路都带着风。 变故是从高二开始的。同学递来的游戏账号,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晚自习偷摸刷副本,午休时躲在楼梯间团战,后来发展到深夜钻被窝看直播——手机屏幕的蓝光,把他的黑眼圈染得越来越深,也把成绩从年级前50,拽到了班级中下游。 “你眼睛不要了?作业写完没?” 母亲第无数次掀他被子时,小凯不耐烦地吼:“别管我!” 罗茂清气得摔门,却在走廊里红了眼——儿子书桌上,那张“物理竞赛省三等奖”的奖状还贴着,可现在,连作业都得靠抄。 高考出分那天,罗茂清请了假,在客厅摆了三盘菜——这是他和妻子偷偷准备的“庆功宴”。可当小凯盯着575分的物理类成绩,把手机一扔:“就这样吧。” 罗茂清的筷子“当啷”掉在地上。 “你知不知道,你是长郡尖子生啊!” 母亲哭着扯他袖子,小凯却冷笑:“尖子生?现在连个一本都够不着。” 这句话像把刀,扎进罗茂清心里——他想起自己在工地上,为了多挣50块加班费,扛着比人高的钢筋爬18楼;想起妻子凌晨三点起来卖早餐,手被蒸笼烫出泡…… “你不走,我们走!” 罗茂清把小凯的行李箱拖到门口,妻子哭着拦,他红着眼吼:“惯着他?这手机毁了他,再惯下去,要毁了这个家!” 小凯没哭,摔门而去,却在小区角落的长椅上,看见父亲蹲在地上抽烟,烟头明明灭灭,像他心里的希望,一点点凉下去。 派出所调解室,空调开得很低,小凯攥着衣角,听父母说“断你生活费,是想让你醒醒”。罗茂清把“两条路”摔在桌上:“要么复读,一年后考个像样的大学;要么打工,自己养活自己,别再碰手机!” 小凯梗着脖子:“你们就嫌我没考上985,丢你们脸!” 罗茂清猛地拍桌,手掌通红:“我在工地搬砖,被监理骂‘没文化’的时候,丢不丢脸?你妈卖早餐,被城管追着跑的时候,丢不丢脸?我们怕的是你一辈子被人看不起,怕你活成我们这样!” 母亲抹着泪补充:“你小时候说‘要让爸妈住大房子’,现在呢?手机里的游戏能给你房子?能给你未来?” 小凯盯着父母粗糙的手——父亲指节上的茧,是搬砖磨的;母亲掌心的疤,是被蒸笼烫的。这些他曾经视而不见的“生活印记”,此刻像针一样扎过来。 其实,罗茂清夫妇“狠心”背后,藏着无数个失眠夜。小凯被赶出门那晚,母亲在阳台守到凌晨三点,看见儿子缩在长椅上,拿书包当枕头,眼泪把围裙都打湿了。罗茂清偷偷塞了200块钱在他书包侧袋,却不敢让妻子知道。 “我们也疼啊,可软的硬的都试过了,他就是离不开手机……” 调解室里,罗茂清声音发颤,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原来,他们不是要逼死儿子,是想把他从手机的“温柔乡”里拽出来,哪怕用最狠的方式。 小凯终于崩溃大哭:“我知道错了…… 高考前三个月,我想戒手机,可一闭眼就是游戏画面,我控制不住啊……” 这话让父母愣住——他们以为儿子是“沉迷”,却不知道,手机成瘾背后,是青春期男孩难以言说的“挣扎”。 调解结束,小凯选了复读。罗茂清夫妇把他送进复读学校那天,母亲往他书包塞了保温杯:“里面是你爱喝的绿豆汤,记得趁热喝。” 罗茂清拍他肩膀:“儿子,这次不是为了985,是为了你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复读班的深夜,小凯把手机锁进学校保管箱,对着错题本上的“物理电磁学”发呆。以前觉得晦涩的公式,现在却像一道道“救赎符”——每解出一道题,他就离那个“被手机毁掉的自己”远一点。 周末回家,母亲会指着他的黑眼圈笑:“比以前在手机里熬的夜,有价值多了。” 罗茂清不再提“985”,只说:“你每天多懂一个知识点,爸在工地就多扛两袋水泥,值!” 这些朴素的话,成了小凯复读路上最暖的光。 小凯的故事,不是个例。在“手机成瘾”“高考内卷”的时代里,无数家庭在上演类似的“撕裂与重生”。父母用“狠心”掩盖焦虑,孩子用“沉迷”对抗压力,可真正的“敌人”,从来不是手机,也不是分数,而是两代人“爱的错位”——父母想给孩子“未来的保障”,孩子却在渴望“当下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