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择水观


茶哲话水
水,生命之源,亦是茶之基质。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
庄子曰:“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天道》
孔子则认为水中有道,“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荀子·宥坐》。
古代的哲人热烈地礼赞水,崇尚水。古往今来,大凡提到茶事的,总是将茶与水联系在一起相提并论的。承扬古代哲人的思想,精茶与真水的融合,才是至高的享受,才能有至上的境界。

古人择水观
在唐代,就有不少专著论述泡茶用水问题,并将古人的经验和调查结论记录下来。唐陆羽在《茶经·五之煮》中阐述了水的选择:“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瀑涌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劲疾。又多别流于山谷者,澄浸不泄,自火天至霜郊以前,或潜龙蓄毒于其间,饮者可决之,以流其恶,使新泉涓涓然酌之。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
明屠隆《茶说·择水》说:“天泉,秋水为上,梅水次之,秋水白而冽,梅水白而甘,甘则茶味稍夺,冽则茶味独全,故秋水较差胜之。春冬二水,春胜于冬,皆以和风甘雨得天地之正施者为妙,唯夏月暴雨不宜。”
明许次纾《茶疏·择水》说:“今时品水,必首惠泉,甘鲜膏腴,至足贵也。往日渡黄河,始忧其浊,舟人以法澄过,饮而甘之,尤宜煮茶,不下惠泉。黄河之水,来自天上,浊者土色也,澄之既净,香味自发。余尚言有名山则有佳茶,兹又言有名山必有佳泉,相提而论,恐非臆说。余所经行吾两浙、两都、齐、鲁、楚、粤、豫、章、滇、黔,皆尝稍涉其山川,味其水泉,发源长远,而潭址澄澈者,水必甘美。即江湖溪涧之水,遇澄潭大泽,味咸甘冽。唯波涛湍急,瀑布飞泉,或舟楫多处,则苦浊不堪。盖云伤劳,岂其恒性。凡春夏水涨则减,秋冬水落则美。”
明张源《茶录·品泉》说:“山顶泉清而轻,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甘,砂中泉清而冽,土中泉淡而白。流于黄石为佳,泻出青石无用。流动者愈于安静,负阴者胜于向阳。真源无味,真火无香。井水不宜茶,《茶经》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最下矣。第一方不近江,山卒无泉水,唯当多积梅雨,其味甘和,乃长养万物之水。雪水虽清,性感重阴,寒不脾胃,不宜多积。”

唐张又新撰《煎茶水记》,记载了陆羽的高超辨水本领:“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维扬,逢陆处士鸿渐。李素熟陆名,有倾盖之欢,因之赴郡,泊扬子驿。将食,李曰:陆君善于茶,盖天下闻名矣,况扬子南零水又殊绝,今者二妙千载一遇,何旷之乎。命军士谨信者,执瓶操舟,深诣南零,陆利器以埃之,俄水至,陆以勺扬其水曰:江则江矣,非南零者,似临岸之水。使曰:其棹舟深入,见者累百,敢虚给乎? 陆不言,既而倾诸盆,至半,陆遽止之,又以勺扬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骇伏罪曰:某自南零赍至岸,舟荡覆半,惧其鲜,挹岸水增之,处士之鉴,神鉴也,其敢隐焉。李与宾从数十人皆大骇愕,李因问陆,既如是,所经历处之水,优劣精可判矣。陆曰:楚水第一,晋水最下。李因命笔,口授而次第之:
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
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
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
峡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泄水独清冷,状如龟形,俗云虾蟆口水,第四;
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
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第六;
扬子江南零水,第七;
洪州西山西东瀑布水,第八;
唐州柏严县淮水源,第九;
庐州龙池山岭水,第十;
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十一;
扬州大明寺水,第十二;
汉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
归州玉虚洞下香溪水,第十四;
商州武关西洛水,第十五;
吴淞江水,第十六;
天台山西南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
郴州圆泉水,第十八;
桐庐严陵滩水,第十九;
雪水第二十。”

此书还记录了刘伯刍对水的评鉴排序:
“较水之与茶宜者凡七等;
扬子江南零水,第一;
无锡惠山泉水,第二;
苏州虎丘寺泉水,第三;
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四;
扬州大明寺水,第五;
吴淞江水,第六;
淮水最下,第七。”
陆羽品南零水而排等次所开创的这场关于茶与水的学术论争,从唐代起一直延续到清代。通过不同学术见解的争鸣探求,引发出了不少关于名茶名水的真知灼见,使人们对饮茶用水的品格有了更高的追求,并拓宽了对茶文化研究的视角范围,这在我国茶学史上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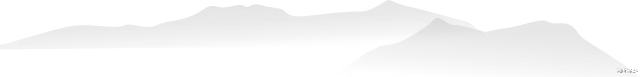
本文来源:图文来自互联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如有侵犯到您的权益,请留言告知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