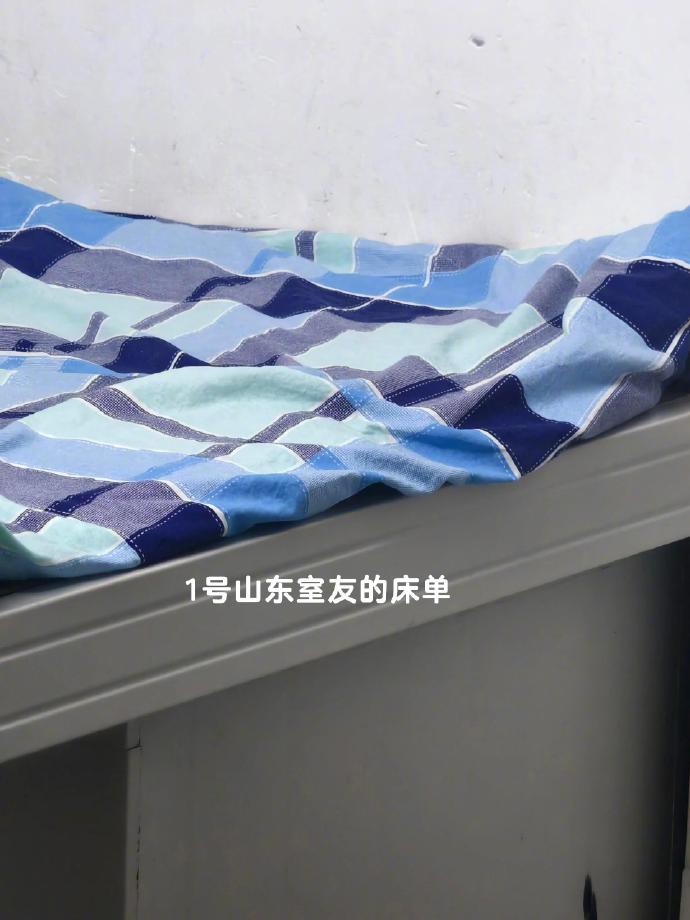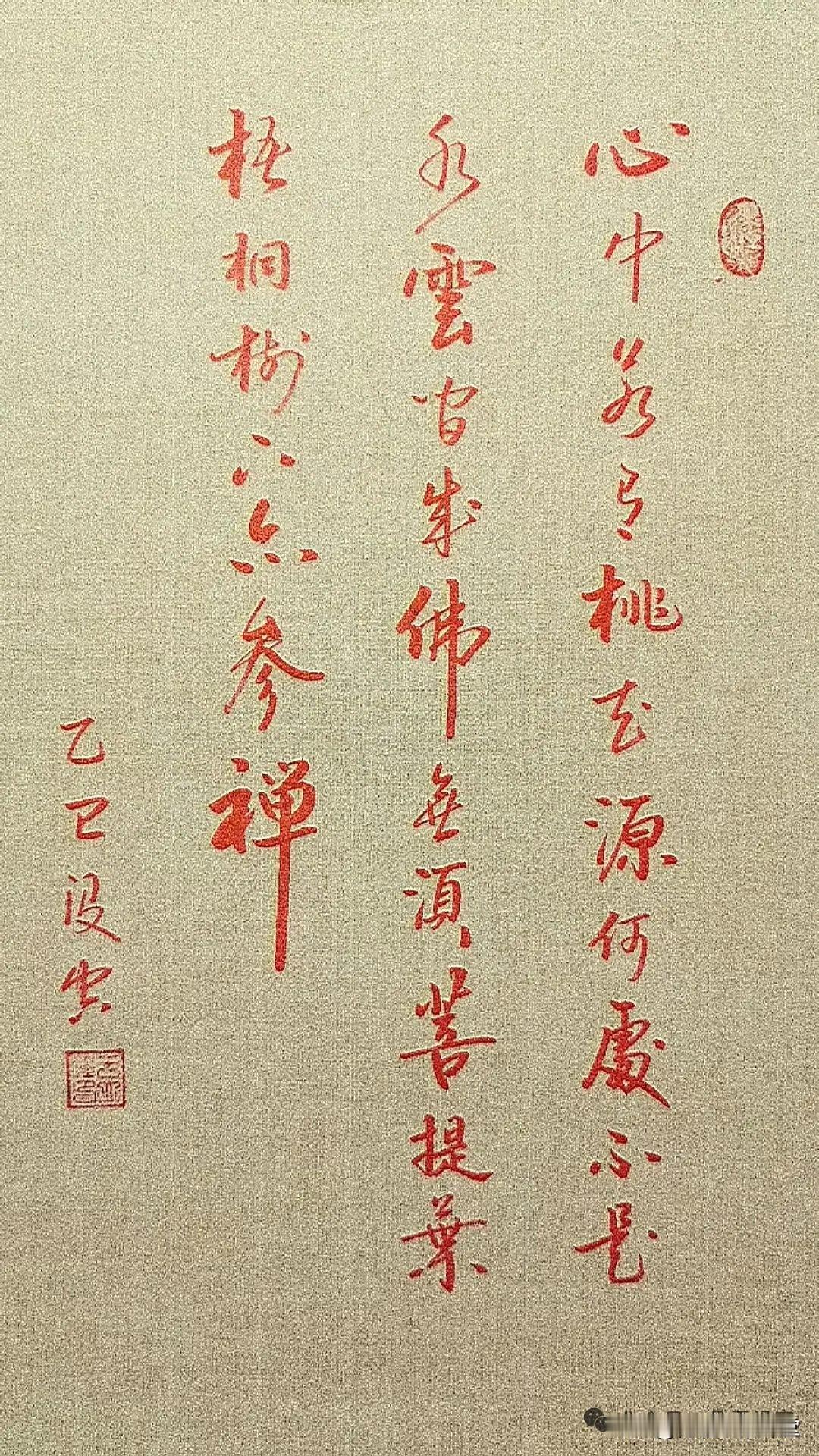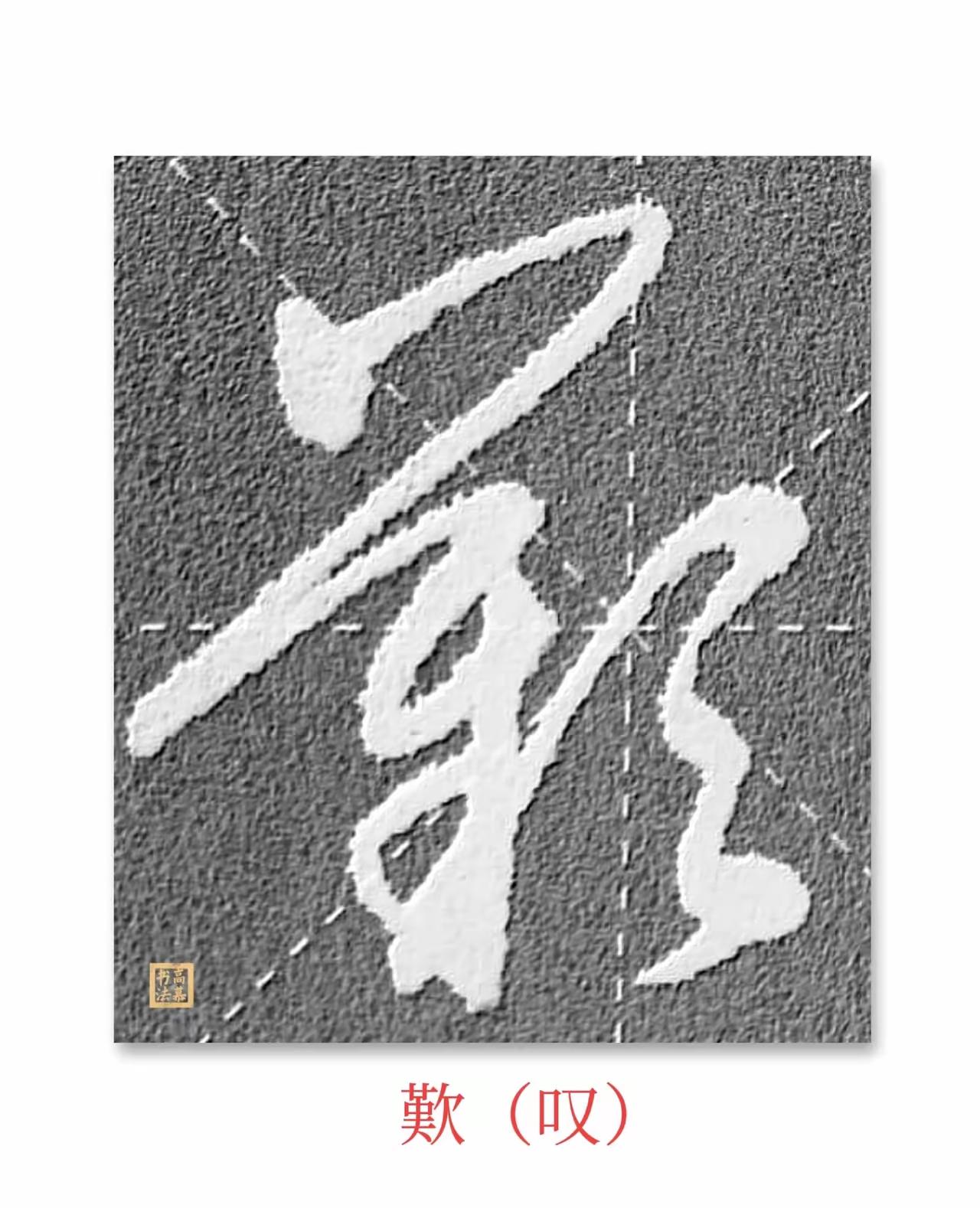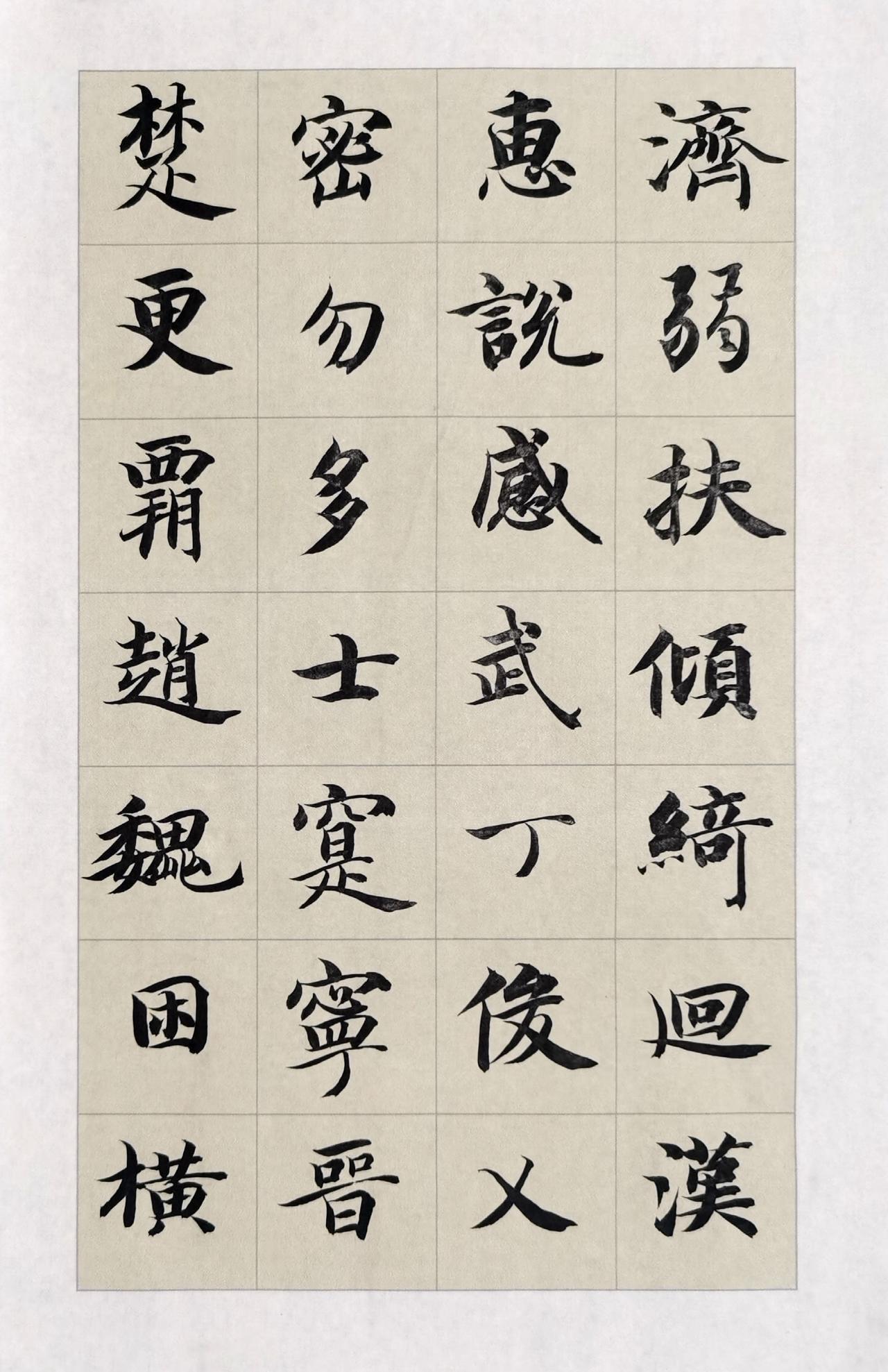老周的笔尖在宣纸上洇开第三滴墨时,窗外的玉兰树正抖落最后一片花瓣。他对着“春风不解离人意”这句反复摩挲,忽然想起三十年前在工厂值夜班,总爱趴在窗台看月亮的自己。 那天在公园长椅上遇到的白衬衫老人,原来真的在老年大学教诗词鉴赏。老周揣着偷偷写的几首打油诗去旁听,当听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时,眼泪突然砸在课桌上——这才惊觉,那些年在车床前重复的机械动作里,他竟错过了无数个可以抬头看云的时刻。 如今他的三轮车筐里总躺着笔记本,菜市场的吆喝声里能听见平仄,晨练的太极步里踩着押韵。有次在社区书法展上,他把《买菜记》写成书法作品:“冬瓜胖,丝瓜长,称杆挑起半斤霜。归途忽见蒲公英,散作星星落夕阳。”围观的老太太们笑出了眼泪,说这诗比电视里的朗诵节目还招人喜欢。 上个月社区举办“银发诗会”,老周站在台上,声音微微发颤:“年轻时总以为诗在远方,到老了才知道,诗就在每天的油盐酱醋里,在孙子打翻的颜料罐里,在老伴补了又补的旧袜子上。”台下掌声雷动,有位戴老花镜的阿姨红着眼眶说:“我丈夫走后,我总觉得日子像没放盐的菜,听你念诗,突然尝到了甜味。” 现在老周的诗集《时光的平仄》已经印了第三版,扉页上写着:“献给所有曾被生活磨平棱角,却依然在皱纹里种星星的人。”他依然每天去公园长椅坐坐,不过现在总会多带一本《唐诗三百首》,遇到迷茫的退休老人,就指着“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说:“您看,这诗是白居易七十岁写的。”退休后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