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台湾作家徐宗懋找到陈阿菊,对他说:“我受你的妹妹朱晓枫托付,前来看看你。”,85岁的阿菊一听,马上警惕起来,态度极为粗鲁。 2005年,一家养老院里,气氛突然变得很僵。作家徐宗懋的到访,像一块石头砸进了死水。他缓缓提起一个名字——“朱晓枫”,而后郑重其事地表明,是她所谓的“妹妹”委托他前来的。 老太太陈阿菊的反应,却像被电击了一样。“我没有妹妹!”她粗鲁地打断,情绪激动。 当徐宗懋又试探着问起“朱枫”时,85岁的老人几乎是咆哮起来:“她是共产党!吾家上下皆为国民党中人,此乃家族之况,与她并无关联!” 这是一种激烈到近乎恐惧的否认。这段曾视如己出的母女情,背后究竟埋藏了怎样的秘密和创伤? 曾几何时,朱枫就是她的整个世界。朱枫本名朱谌之,在嫁给陈阿菊的父亲陈绶卿时,陈阿菊才七岁。 身为继母,朱枫将她视若己出,以毫无保留的深情,倾尽全力地给予她如潺潺溪流般细腻、如春日暖阳般温暖的母爱。哪怕后来丈夫离世,她也依然尽心尽力地抚养着前夫留下的孩子。 这段温情在一个米缸前戛然而止。1950年初,朱枫以探望初诞爱女的名义奔赴台湾,彼时,陈阿菊的家便成了她在台的安身之所。 可这个“母亲”太奇怪了。她说去市场,回来时鞋底却干净得没有一丝泥。她常在家里烧东西,还鬼鬼祟祟地在米缸里藏匿物件。 对于丈夫是国民党特务的陈阿菊来说,这些迹象让她不寒而栗。她明白了,眼前的养母,不再只是家人。亲情和恐惧,在她心里打了一架。 最终,恐惧占了上风。她并未告密,只是近乎哀恳地劝朱枫搬走,她所求不过是保全自己那一方小小的安乐窝罢了。 讽刺的是,这种自保并没能换来安宁。朱枫最终因同志叛变而被捕牺牲,而陈阿官夫妇也受到牵连,被关押了数月。此般抉择,宛如沉重枷锁,自此紧紧缚于她身。这枷锁,成了她一生难以挣脱的负累,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朱枫的死,在海峡两岸催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回响。在大陆,她的第二任丈夫朱晓光,一位比她小11岁的中共地下党员,用尽余生寻找妻子的骨灰,却至死未能如愿。 2000年,他抱憾离世,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儿子朱明和女儿朱晓枫。 这是一场公开的、充满荣誉感的追寻,是一个家庭必须完成的使命。 而在海峡的另一边,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沉默。陈阿菊不是没想过去申领养母的骨灰,但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这个念头足以致命。恐惧像一层厚厚的茧,将她和过去彻底包裹起来。于是,她只能选择遗忘和否认。 但那句在养老院里下意识问出的“她有没有遭罪”,还是暴露了压抑了几十年的情感。这两种纪念方式,一个轰轰烈烈,一个讳莫如深,共同勾勒出那个时代撕裂人性的残酷真相。 转机出现在2001年。朱晓枫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杂志上,偶然看到了一张母亲牺牲时的照片。这张照片,由台湾作家徐宗懋提供。他成了连接两个家庭、跨越海峡的关键桥梁。 徐宗懋耗时两年在台湾奔走,一无所获,直到他决定去寻找那个被刻意遗忘的名字——陈阿菊。正是那场看似失败的会面,陈阿菊在激烈的否认中,无意间透露了一个关键线索:骨灰后来被“政府”收走了。 这成了最后的拼图。 2010年,朱枫的骨灰终于被找到。次年7月12日,在复杂的交接后,英魂跨越海峡,回到了宁波。在栎社国际机场,朱晓枫、朱明姐弟紧紧抱着母亲的骨灰坛,这场阔别了六十余年的团聚,终于以另一种形式实现了。 信息来源:女地下党在台牺牲60年后回家 80岁女儿托人寻母——2011-01-02 08:25:06来源:扬子晚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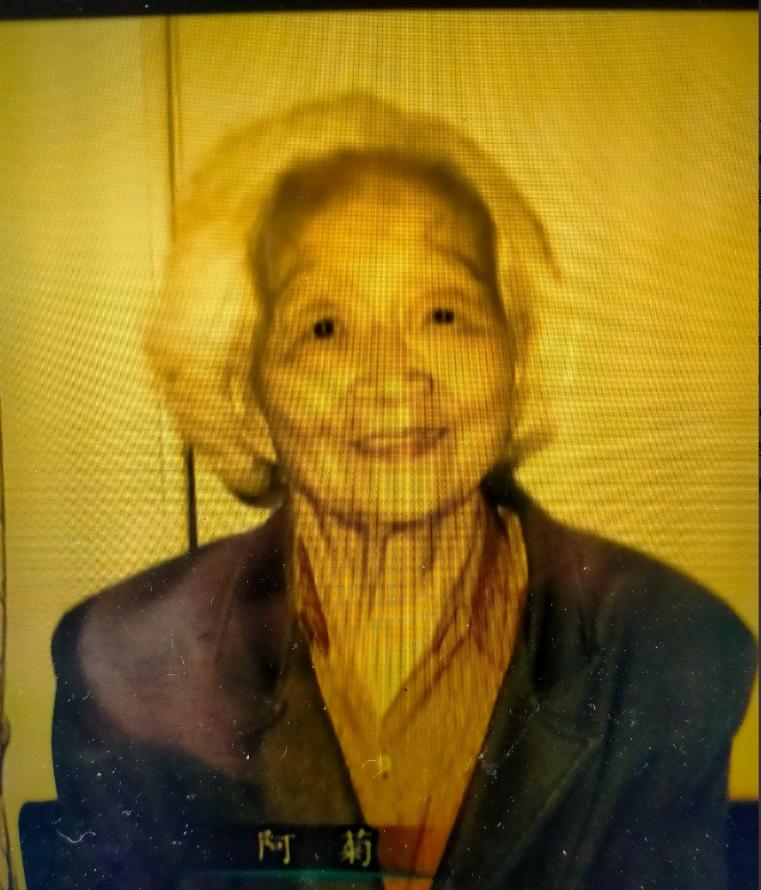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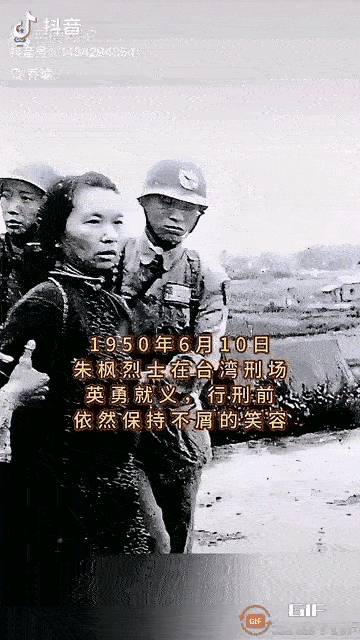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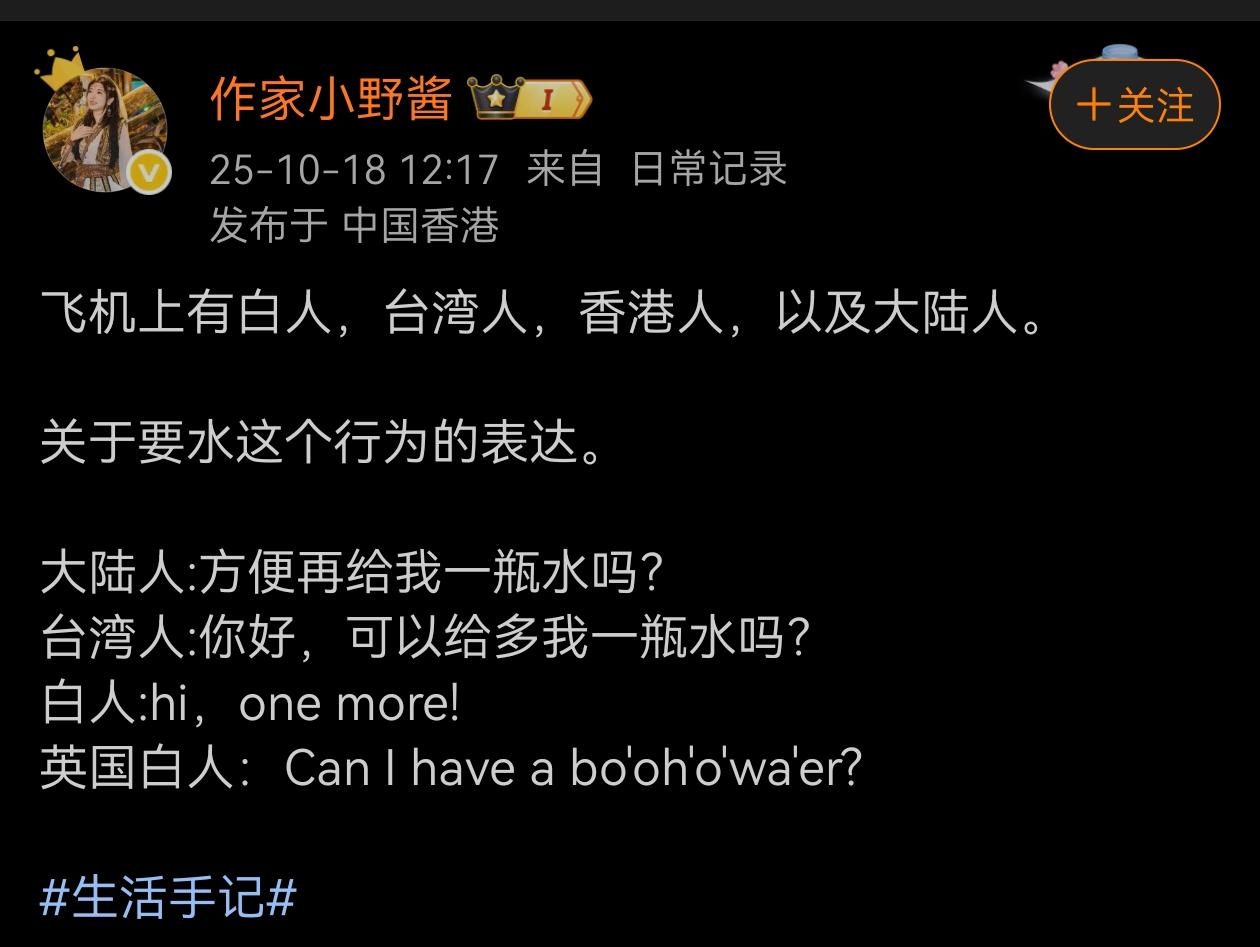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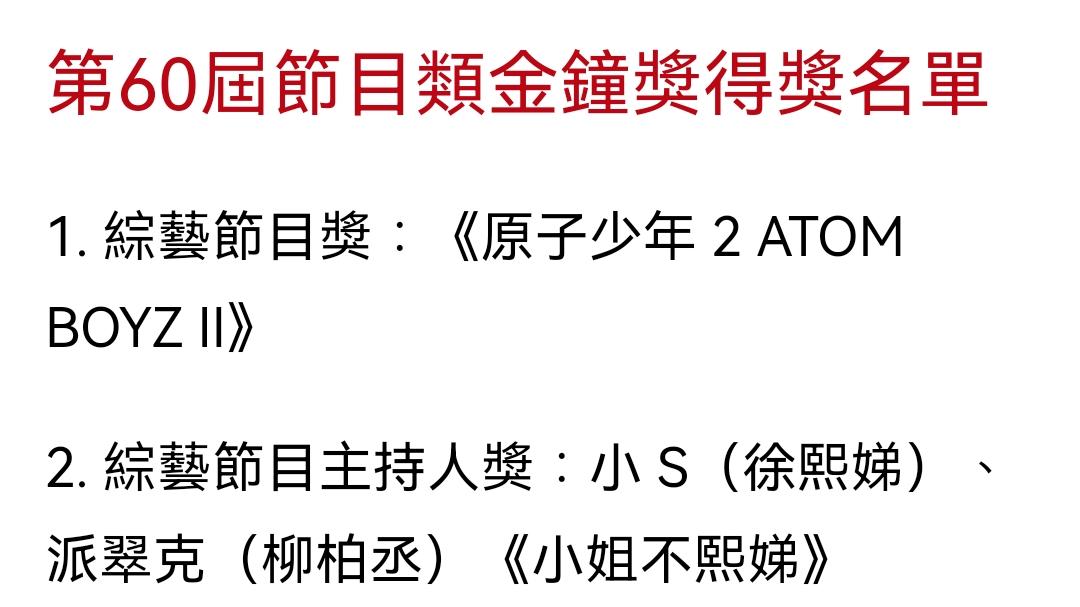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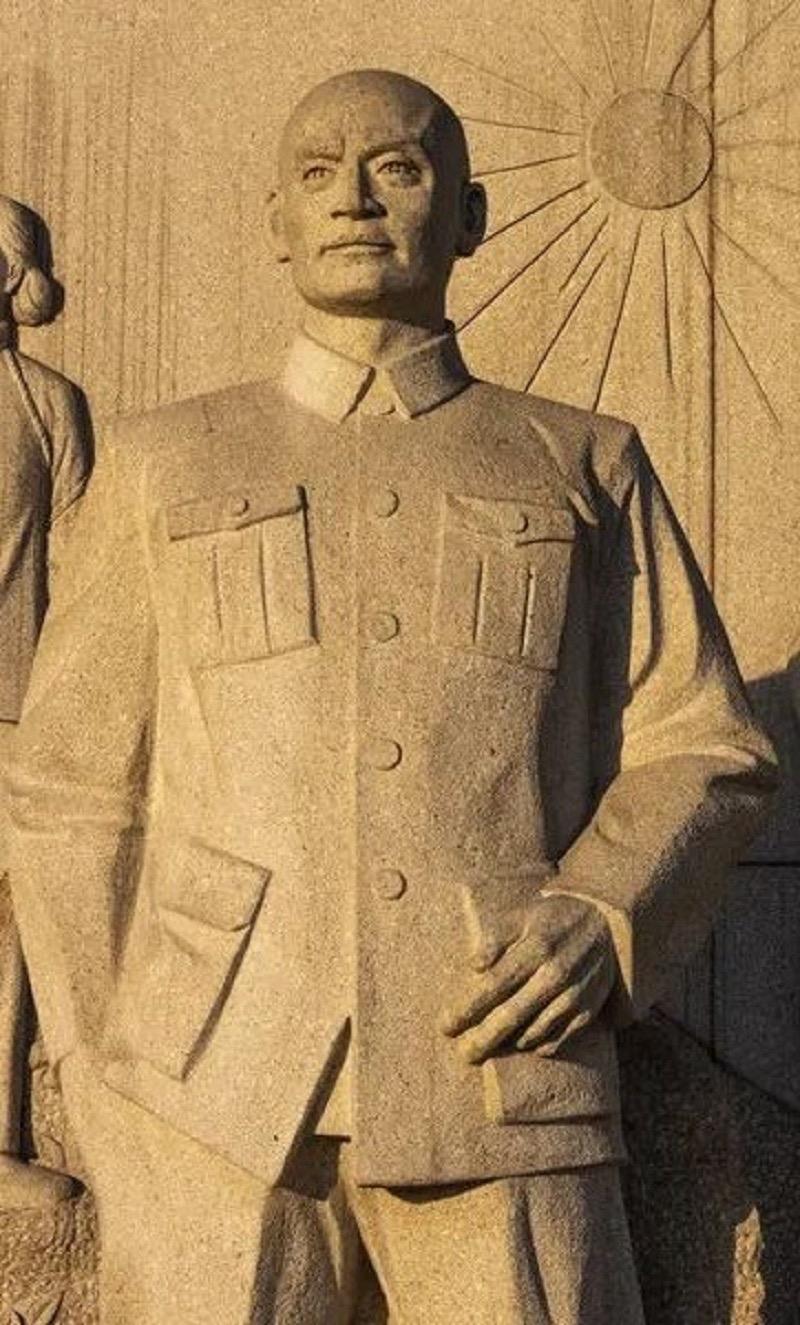

皓月
朱枫烈士永垂不朽![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