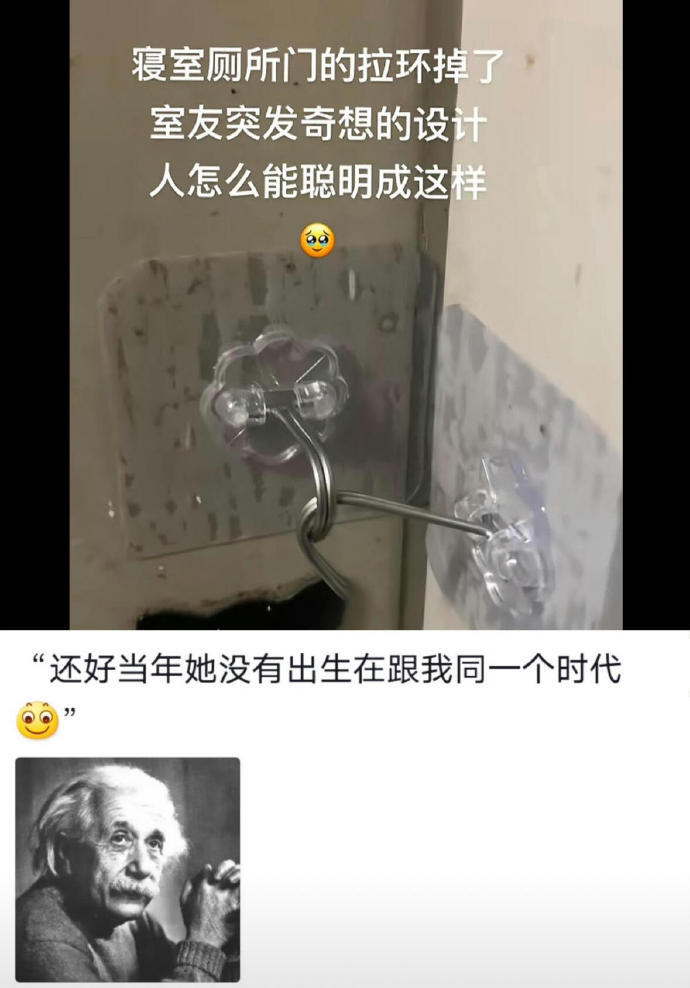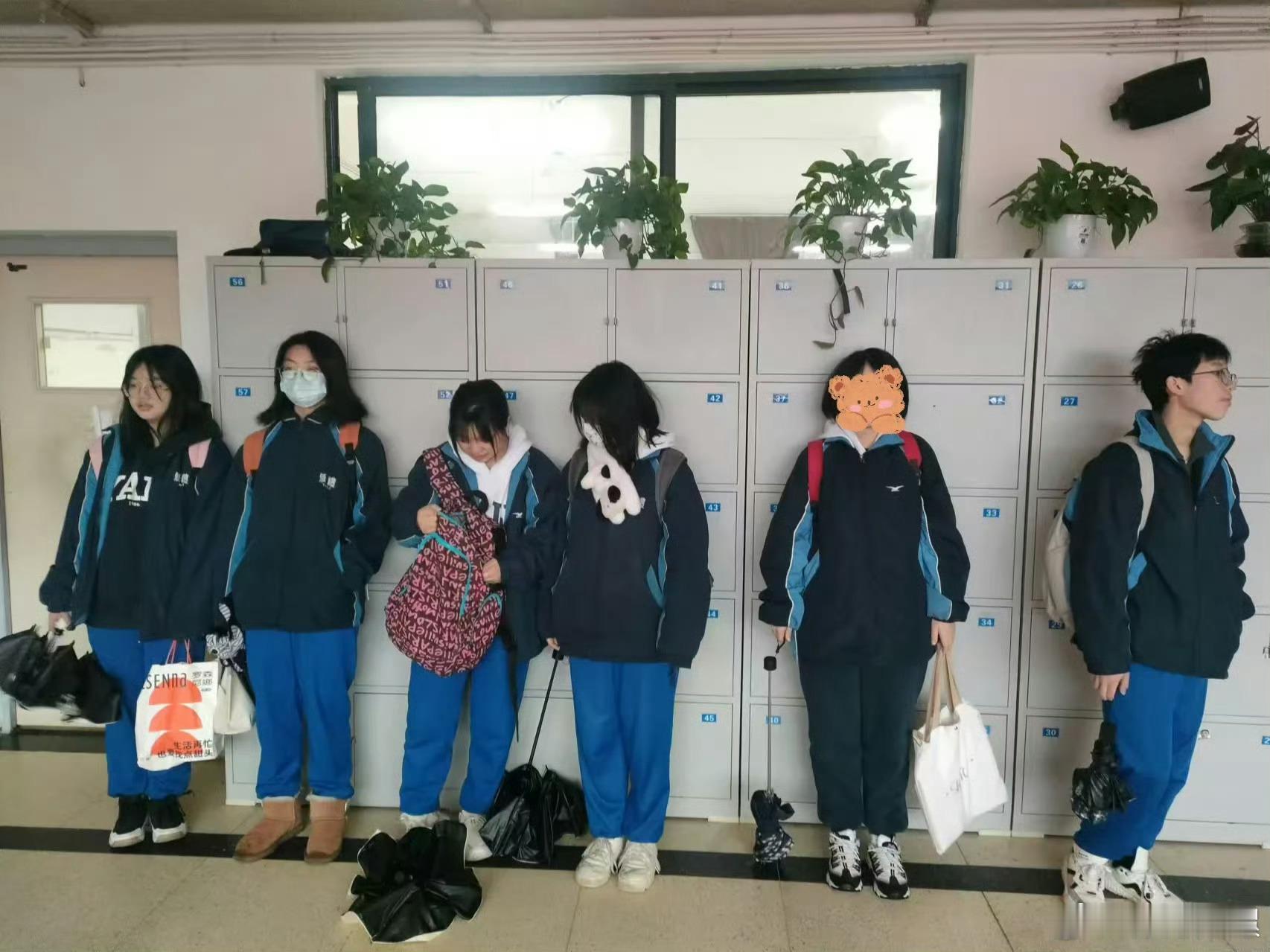近日在浙江大学发生了感人的一幕,一位巴东学子“向东升”,在陈行甲结束演讲后,怯生生地找到他,俩人拥抱交谈,男孩忍不住落泪。 秋日的浙江大学,课后的走廊里还残留着课堂的余温,阳光透过窗户,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刚结束授课的陈行甲,正低头整理教案,准备离开教室。 他这次是受浙大邀请来做专题分享,身上还带着刚讲完课的些许疲惫。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灰色运动服的男生,犹豫着停在了他面前。 男生看起来有些紧张,手指不自觉地攥着书包带,沉默了几秒才开口,声音不大却很清晰:“陈书记,您……您还记得巴东吗?” 陈行甲听到“巴东”两个字,整理教案的手猛地一顿,他抬起头,看向眼前的男生。 起初眼神里带着几分疑惑,几秒后,当他看清男生的模样,疑惑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难以掩饰的惊喜。 “你是……从巴东来的孩子?”陈行甲往前迈了一步,语气里满是意外,紧接着又追问,“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会在浙大读书?” 男生连忙回答:“我叫向东升,去年从巴东县考进浙大的。” 之前听说今天授课的老师是您,就特意留下来,想跟您打个招呼。” “向东升……”陈行甲在嘴里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眼睛亮了起来,“巴东有‘谭田邓向’四大姓,你是向家的孩子吧?” 得到男生肯定的答复后,他又急切地问,“当年你在巴东参加高考,名次是多少?” “全县第五名。” 向东升话音刚落,陈行甲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上前一步伸出手,一把将向东升抱住,手掌轻轻拍着他的后背,语气里满是感慨:“不容易啊,孩子,太不容易了。” 被抱住的向东升,鼻子一酸,眼泪瞬间涌了上来,顺着脸颊往下掉,砸在陈行甲的肩膀上。 他想说些什么,却发现喉咙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任由眼泪释放着这些年藏在心里的辛苦。 陈行甲能感受到肩膀上的湿润,他没有松开手,反而抱得更紧了些。 他太清楚这眼泪里藏着什么——那是一个山里孩子,为了走出大山,付出的无数个日夜的艰辛。 过了好一会儿,两人才慢慢松开。 陈行甲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拉过向东升的手,把自己的手机号存进了他的手机里,还特意叮嘱:“以后在学习上、生活上遇到任何困难,别客气,随时给我打电话,能帮的我一定帮。” 他还不忘追问向东升,浙大里还有没有其他从巴东来的学生,要是有的话,可以一起联系,有机会大家聚一聚,互相照应。 向东升握着手机,用力点了点头,眼泪还挂在脸上,却露出了笑容。 他知道,眼前这位曾经的巴东县委书记,是真的懂他,真的牵挂着巴东来的学子。 其实,陈行甲对巴东学子的牵挂,早在多年前就刻进了心里。 2011年,39岁的他到巴东任县委书记,面对的是一个有五十万人口、十七万贫困人口的山区县。 除了大刀阔斧反腐,查处八十七名违法官员、清退两百零六个吃空饷人员,他最上心的就是山区教育。 他跑遍了巴东的山区学校,看到孩子们在漏风的教室里冻得瑟瑟发抖,在闷热的夏天汗流浃背,心里不是滋味,便四处奔走争取资金,翻修教室、添置设备,还常跟孩子们说“巴东孩子没别的路,读书才能走出大山”。 后来陈行甲辞去县委书记职务,转做公益,2021年出版自传时,还在书里写下对巴东孩子的牵挂,承诺售书收入全部捐给贫困重病儿童。 如今在浙大遇见向东升,这份牵挂有了最直接的回应。 而向东升能从巴东深山走到浙大,靠的也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冬天裹着两层旧棉袄在漏风教室做题,夏天在闷热屋里汗湿课本,每天天不亮就着路灯背书,深夜躲在走廊刷题,三年下来错题本堆得半人高。 这样的相遇,让人想起云南华坪女高的张桂梅校长。 她在深山办学二十多年,守护着山里女孩的求学梦,那些考出去的学生见到她,也会像向东升见到陈行甲一样红了眼眶。 如今,向东升在浙大继续努力,陈行甲在公益路上奔走。 这场发生在浙大走廊里的偶遇,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最真挚的情感,连接起了巴东的深山与浙大的校园,也让人们看到,真心的牵挂与付出,永远会有温暖的回响。 那么到最后,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如果各位看官老爷们已经选择阅读了此文,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