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不受各种意志约束,能够“吾手写吾口”,并且敢于质疑和反思,就已经尽到了一个作家的责任,无愧于“作家”的称号了!而有些人对作家道德上的指责,是对其个人人格的侮辱,是恶毒和残忍的,尤其是这种指责只凭着似是而非的借口。莫言的获奖无关于政治,也无关于他“体制内”的身份,我们不必为此而苛责他。 学者张旭东也说:“莫言获奖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并没有兴趣去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没有表现出一种脱离中国社会创作的形象。他有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能够享受的权利,也分担所有人都受到的限制,因此诺贝尔文学奖是个有政治立场的奖,但说到底还是个文学奖,这些作品没有哪一部是在别人的授意之下,按照他人的意志来写的。” 在莫言的童年时代,乡村文化生活相对匮乏,说书便成为了村民们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 。那时,集市是说书的重要场所,每逢集日,说书艺人便会在集市上摆开场子,吸引众多村民前来聆听。他们凭借一把折扇、一块醒木,再加上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表情,就能将一个个精彩的故事演绎得活灵活现。这些故事涵盖了历史传奇、民间传说、英雄事迹等诸多方面,内容丰富多样,让听众们如痴如醉。 莫言对听书充满了痴迷。他常常偷偷跑去集市,从成年人的腿缝里钻进场子,全神贯注地听那些说书艺人说书 。在他的回忆中,集市上的说书人说的山东快书武老二,大鼓书里的杨家将、岳飞故事以及茂腔戏里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故事,都令他着迷上瘾。这些故事就像一把把钥匙,为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带他走进了一个充满奇幻与想象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结识了许多英雄豪杰和奇人异士,感受到了他们的豪情壮志和传奇经历。 为了听书,莫言甚至会忘记母亲分配给他的活儿 。有一次,他偷偷跑去听书,结果忘记了回家做饭,母亲为此批评了他。但他对听书的热情并未因此减退,晚上,当母亲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他忍不住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绘声绘色地复述给母亲听。起初,母亲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腔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莫言复述的故事却渐渐吸引了母亲,她被那些精彩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所打动,从此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莫言排活儿,默许他去集市上听书。 莫言的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她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敏锐的感知力 。她一方面为儿子的口才和想象力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对他的未来感到担忧。她常常忧心忡忡地对莫言说:“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母亲的这句话,从侧面反映出莫言在讲故事方面的天赋和热情 。在那个时代,能说会道的人往往被视为不务正业,母亲的担忧也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观念。但莫言对故事的热爱并没有因为母亲的担忧而减退,反而更加激发了他对创作的探索和追求。 这些经历对莫言的叙事能力培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复述和改编故事的过程中,他学会了如何组织语言、构建情节、塑造人物 。他开始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讲述同一个故事,体会不同的叙事方式所带来的效果差异 。这种训练让他逐渐掌握了叙事的节奏和技巧,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学会了如何运用生动的语言描绘场景,如何通过人物的对话和行动展现其性格特点,如何设置悬念和冲突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这些叙事技巧在他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使他的作品充满了魅力和张力。 莫言对这些传统说书曲目耳熟能详,他沉浸在这些故事的世界里,被其中的人物和情节所吸引 。这些故事中的英雄人物、传奇情节和民间智慧,成为他小说创作的重要养分 。在他的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这些传统说书故事的影子 。例如,在《红高粱家族》中,余占鳌等人物的形象和行为,就有着绿林好汉的特征,他们勇敢无畏、敢于反抗,充满了野性和生命力 ,这与传统说书中的英雄人物形象相呼应 。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也充满了传奇色彩,如余占鳌带领队伍抗击日寇的故事,充满了紧张刺激的战斗场面和英雄主义情怀 ,与传统说书故事中的战争场面和英雄事迹有着相似之处 。 在《檀香刑》中,莫言更是将高密茂腔这一地方戏曲融入小说创作 。高密茂腔是高密、东北乡文化的精粹,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和民间性,其简约质朴、婉转悠扬的唱腔风格和通俗简洁的艺术表演形式,成为莫言小说中独特的文化符号 。 小说中,莫言通过对茂腔的描写和运用,展现了高密地区的地域文化特色,使小说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 。他还借鉴了茂腔的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法,使小说的情节更加生动曲折,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立体 。例如,小说中通过茂腔的唱词来表达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使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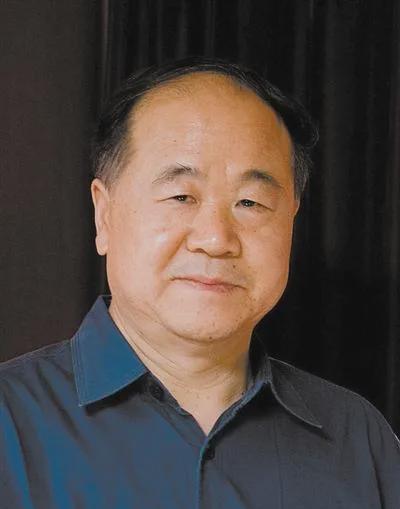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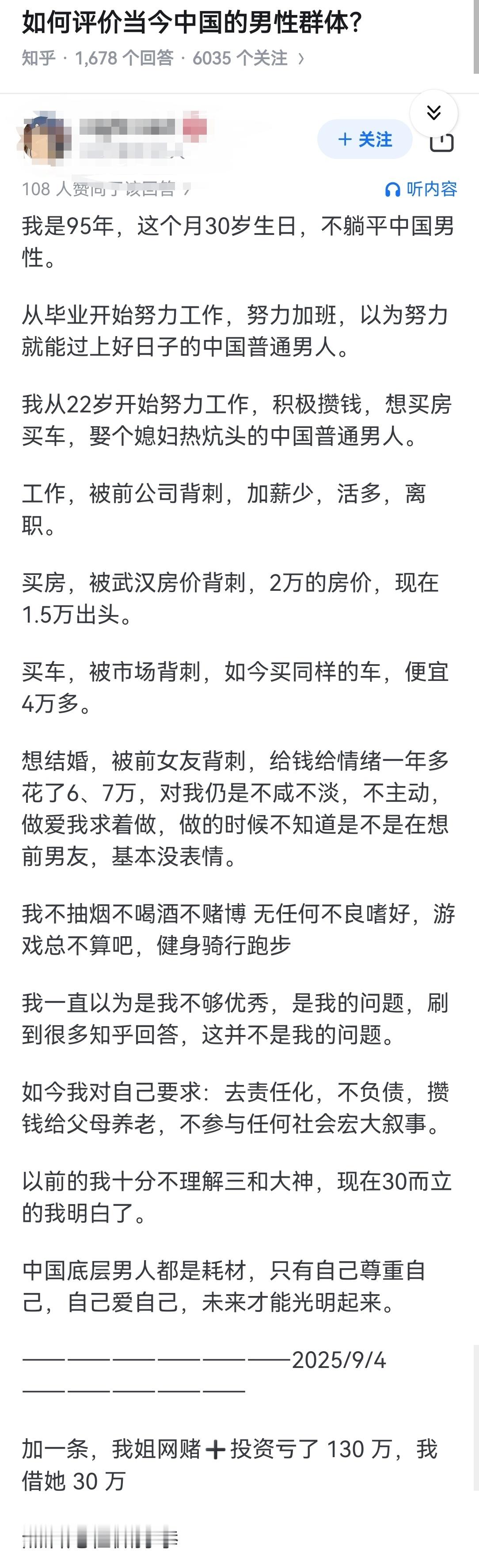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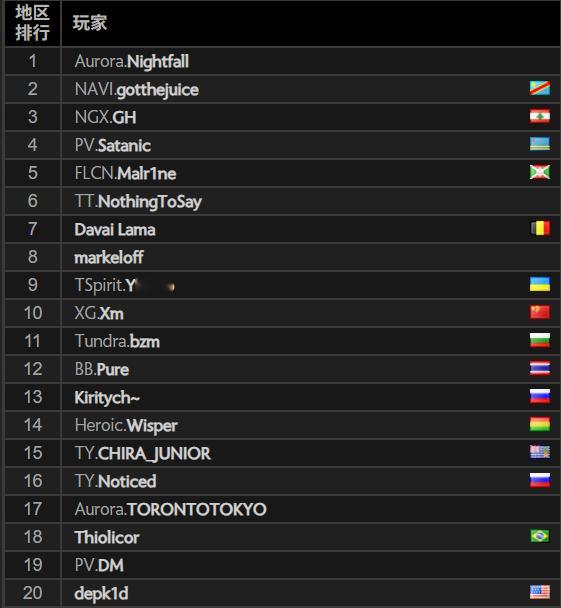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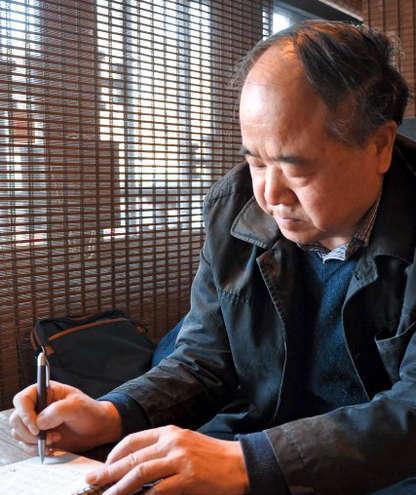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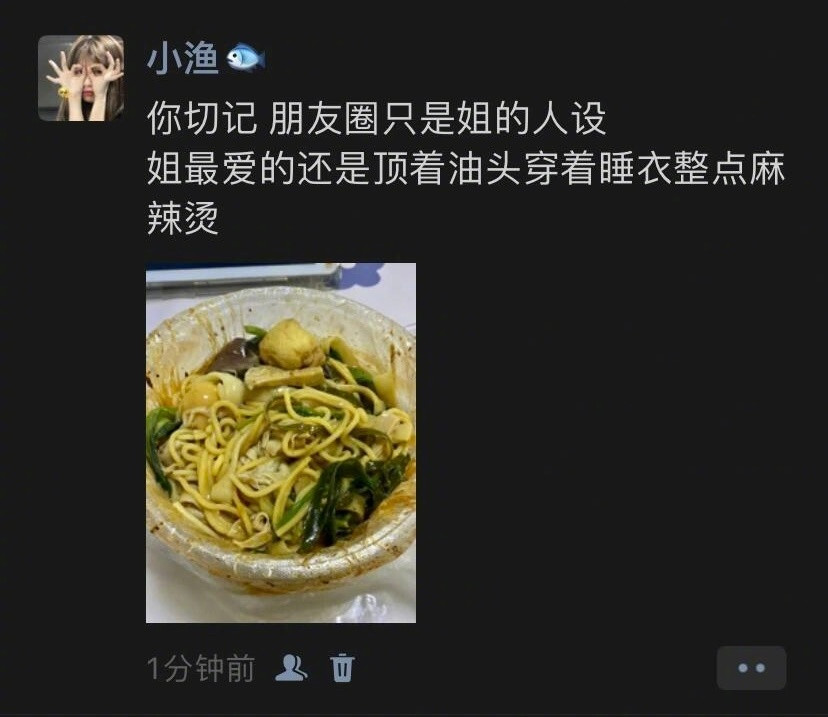
![完全没印象有些人播过这么多戏[笑着哭]](http://image.uczzd.cn/788516219423236712.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