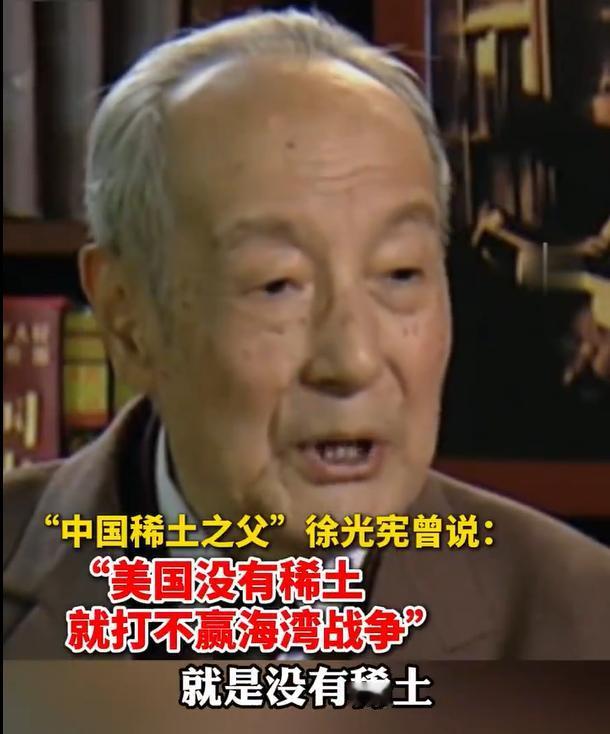红色之都的江西,出了五位能征善战的开国虎将,他们都是谁 “1955年9月27日的怀仁堂里,老梁,这回可把咱江西的虎将都聚在一个屋檐下了。”有人打趣。梁兴初放下军帽,压低声音回了句:“别闹,打仗看拳头,不看门牌。”不到三秒,场内便复归肃穆。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授衔典礼,将江西这块被称作“红色之都”的土地再次推向镁光灯中央。 追溯时间,1927年的南昌、1928年的井冈山、1931年的瑞金相继燃起星火,江西成了革命的实验田。红军在这里首创“支部建在连上”,也在这里练出一批敢战善谋的年轻人。抗战爆发、解放硝烟、到朝鲜山岭上的呼啸炮声,江西子弟几乎场场未缺席。把目光锁定在李作鹏、梁兴初、丁盛、曾思玉、温玉成这五个名字,人们才惊觉:同一省份竟能同时孕育如此密集的“军旅尖刀”。 先说李作鹏。1930年,他还是吉安一名17岁学生,听到“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便卷起铺盖进山。参加过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时担任团参谋长,蹚过乌江天险,翻越雪山草地。东北解放阶段,他因为一场酒后争执被林彪贬到第六纵队,可仅用三个月就把十六师练成“穿林海、跨雪原”的先遣尖兵。1949年春,第43军横扫粤桂,随后渡琼州海峡拿下海南岛——陆海协同、夜暗潮急,硬是让敌方守军误以为对面至少来了一支海军。战后有人统计,全军伤亡比为一比九,李作鹏这个数据至今仍被军校教材引用。 再看梁兴初。1930年秋加入红军,他的履历像拉满弓的箭:反“围剿”——抗战——解放——入朝,一气呵成。东北冬夜零下三十度,他让战士把冻得发脆的土豆切成薄片塞进怀里,“硬了啃不动,捂热了还能填肚子”。三下江南到广西,都说四野部队推进速度是“铁路第零纵队”,可梁兴初的第38军往往还能领先半天。入朝后,三十八军于龙源里包围韩、土两国王牌旅,截断敌南逃通道,彭德怀一句“万岁军”从此写进史册。 丁盛是后来者,却是狠角色。于都县的山路把他的脚板磨出血泡,他却摆手说:“流血是提醒我别停。”1947年夏季攻势,他的第1师在索伦山正面突破,连续攻下六座制高点,被四野总部点名嘉奖。1949年接过第54军旗帜,这支组建仅百余天的新军在湘桂之役俘虏七万余人,接着进军西南、高原灭匪、再远征朝鲜,一支枪配出“四用”:打正面、清残匪、守要塞、救急援。丁盛因此被部队戏称“救火队长”。 谈起曾思玉,冀中老乡常说一句话:“仗打到村口,你能听见曾军长的哨声。”出身信丰的他,1933年提拔连长,雁门关伏击战以三百人缠住日军两千五,硬生生拖到援军赶到。解放华北时,他率64军昼夜奔袭350里,切断北平通往张家口的最后铁路线。敌人仓促撤离,满地丢下成排火炮。杨得志拍着他肩膀:“这才叫步兵的速度。” 温玉成则是另一种画风。兴国穷,父亲卖掉半亩田给他置办行囊,他就此踏进红军队伍。长征过草地那晚,他悄悄把传令兵的旧棉衣披在腿上,自己只穿薄单衣继续趟沼泽。东北野战军时期,第40军以快制胜,辽沈决战发起日,温玉成带队抄敌后路,活捉整旅指挥所。1950年赴朝,40军首战云山,车轮式攻击打得美骑一旅惊叫“东方的幽灵”。志愿军总部统计,40军歼敌最多、伤亡最小,温玉成被列入“十大虎将”。 有意思的是,这五人虽同省,却在完全不同的岗位展示各自锋芒:参谋长出身的李作鹏转型野战军长;梁兴初擅长大兵团穿插;丁盛抢攻、曾思玉奔袭、温玉成侧翼渗透,各有绝招。其中四人出自东北野战军并非偶然。东北广阔、气候恶劣,适者生存的淘汰机制逼迫指挥员练就“夜行五十里不迷路,三天无给养不散伍”的硬功。江西子弟早年就习惯山水崎岖,加之井冈山斗争积累的游击经验,与东北野战军对快节奏、大穿插的要求恰好契合,这种背景碰撞,才让“江西猛将”这一标签在四野、在志愿军里频频闪光。 值得一提的是,五支王牌军之间曾有多次默契配合。辽沈战役,38军与40军互为犄角;海南岛战役,43军先渡海,54军负责后勤接应;平津前线,64军穿插切割后,38军顶上正面。外界感叹:江西将领不但单打独斗行,团体作业也漂亮。 资料显示,解放全程,有141名江西籍将领获得授衔,其中大部分在连级、营级就历经反“围剿”锤炼。从基层摸爬滚打到麾下十万之众,路径不同,底色一致——血性。战争结束多年,那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劲头仍留在训练场、留在教科书、留在后辈口口相传的“江西样本”里。 回到典礼现场,授衔结束,礼炮轰鸣。有人好奇问梁兴初:“你们江西怎么出了这么多打仗的?”他摆摆手:“老家山多田薄,不拼不行。可真到枪口相对时,谁都得拼。”一句朴素的回答,道尽了“红色之都”最原始的动力——生存与信念交错,孕育出一代代能征善战的虎将。

![于正要演将军了[笑着哭]](http://image.uczzd.cn/10775405504116759187.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