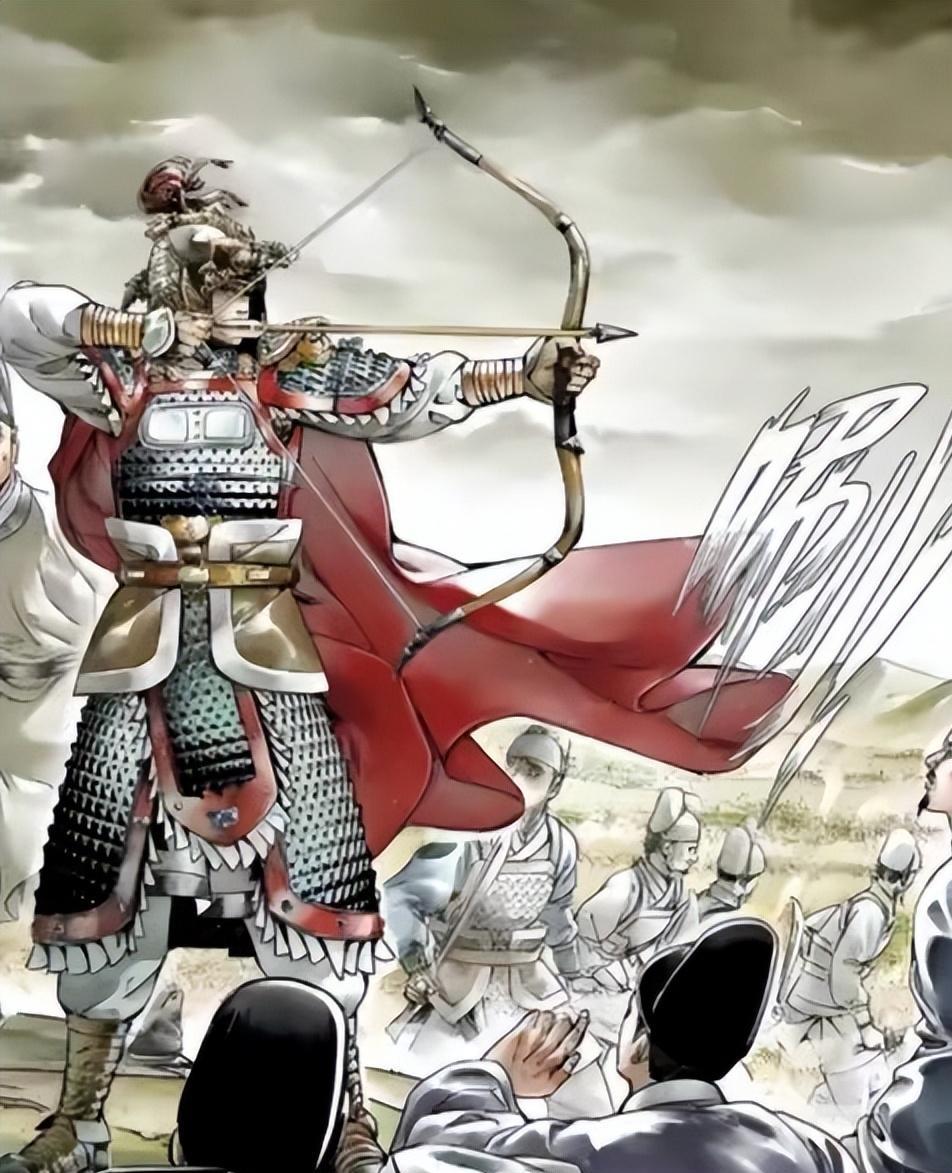雪地里,锅才架好,柴火冒了烟,米粒倒进锅里,热气刚起,探马报进营门,马蹄声急促,脸色煞白,只吐出两个字——“契丹!”火苗立刻被压下,锅盖合上,营地的气息瞬间冷了。曹彬握着缰绳,眼神沉下来。几个月的北伐,几百里的推进,眼看胜局在握,却在这口饭没煮熟时,崩成了散沙。这一仗,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东风正劲的时候,曹彬率着东路军从雄州杀出来。那是三月的早晨,雍熙北伐三路齐发,东路最先起势。雄州城门早早打开,兵马如洪水般涌出,铁甲反着朝阳,旗帜在寒风中猎猎作响。城外百姓站在土坡上看着队伍,耳边是马蹄和鼓声,心底涌起一股子壮烈。 涿州、固安,一路攻下,旗子换得干脆。宋军马蹄在冰雪混合的道路上敲出密密的节奏,连契丹的耳目都跟不上变换的速度。前锋一次次探路,传回的消息总是一样:契丹避战、撤走。 这对东路军来说有好有坏。好在推进无阻,坏在主力迟迟碰不到,补给线被拉得越来越长。运粮的车队在结冰的驿道上走得极慢,车轮碾过硬雪,发出刺耳的响声。半路上,还得提防契丹轻骑的偷袭。几次粮车被劫,士兵们的饭量便跟着减。 曹彬心里清楚,眼下最大的敌人不是契丹,而是粮。押运队损失惨重,有的车被烧,有的连人带粮消失在风雪里。辽军不打正面,就像狼群咬牛腿,死死咬住补给线。几次丢粮之后,米袋见底,马料掺糠,士兵啃着硬得能硌掉牙的馍干。天冷,肚子空,眼神里多了疲意。 涿州一带,推进不得不停下来。曹彬下令暂缓北进,先让部队喘口气,生火做饭。锅刚架好,米下锅,热气才腾起几缕,探马便从北口冲回,马蹄在雪地里掀起泥点。契丹骑兵又逼近,比风还快。 锅盖重新扣上,火被踩灭,兵器重新握在手里。曹彬知道,这不是硬拼的时候。疲兵对精锐,胜算太低。唯一的办法是撤,撤回雄州保住实力。命令一到,营地立刻忙乱起来,锅推翻,旌旗卷起,辎重收好。队列拉得很长,前面是车,后面是步兵,外围是一圈马队。 契丹骑兵像影子一样紧跟,不急着正面冲阵,先迂回、骚扰。狼群的耐心,让宋军不得不频繁停走、变阵。盾牌立起挡箭,弓弩架在车旁戒备。几次短兵接触下来,宋军伤亡渐多,粮食洒在雪地里,很快被追兵抢走。 撤到拒马河一带,河面覆着薄冰,必须渡过去才能挡住追兵。最乱的时刻就在渡河。冰面碎裂,士兵和马掉进冰水里,兵器在水中发出沉闷的声响。有人拼命游,有人挣扎着抓同袍的手,却被湍急的水流冲走。拒马河的水,被血染得发暗。等到冰面重新结上薄层,喊杀声才渐渐停下。 这一路能撑到雄州,全靠李继隆带后军死守。他选了最窄的路口,硬生生用盾阵挡住辽军的锋头。箭雨打在盾牌上,像豆子落在铜盘上。阵里的人轮换着上阵,手臂酸到发抖,却不敢松。辽军冲不进去,便绕到两翼,再被步兵用拒马钉拦下。正是这几道防线,换来主力安全撤回。 回到雄州时,东路军的士气已被冷风和饥饿磨得七零八落。城墙下的百姓看着这些满脸风霜的士兵,悄声议论着北方的战事。 京师里早就传开捷报,说北伐势如破竹。可当曹彬带着残部回报时,胜利成了败绩。宋太宗的心情像被泼了冷水,原本的三路夹击计划彻底落空。 曹彬心里最清楚,失败不在于兵不行,而在于粮草被掐得太死。北方的仗,不只是拼刀剑,更是拼长线。断了粮,刀再快也会钝。 撤回之后,他上奏承认失策。那句“本可成功,而为所败”,是实话。他清楚,只要补给不断,涿州之后,幽州并非不可及。可现实是,辽军的骑兵一旦切断粮道,宋军的攻势就像被拧紧的绳子突然松开,一下子散了。 雍熙北伐的东路,就这样收在一口没煮熟的饭锅里。北风还在刮,河道还在冻,契丹的马蹄声在夜里像梦魇一样绕着雄州城转。曹彬站在城头,风中混着炊烟和战火的余味,那一声慨叹,吹进了所有人的耳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