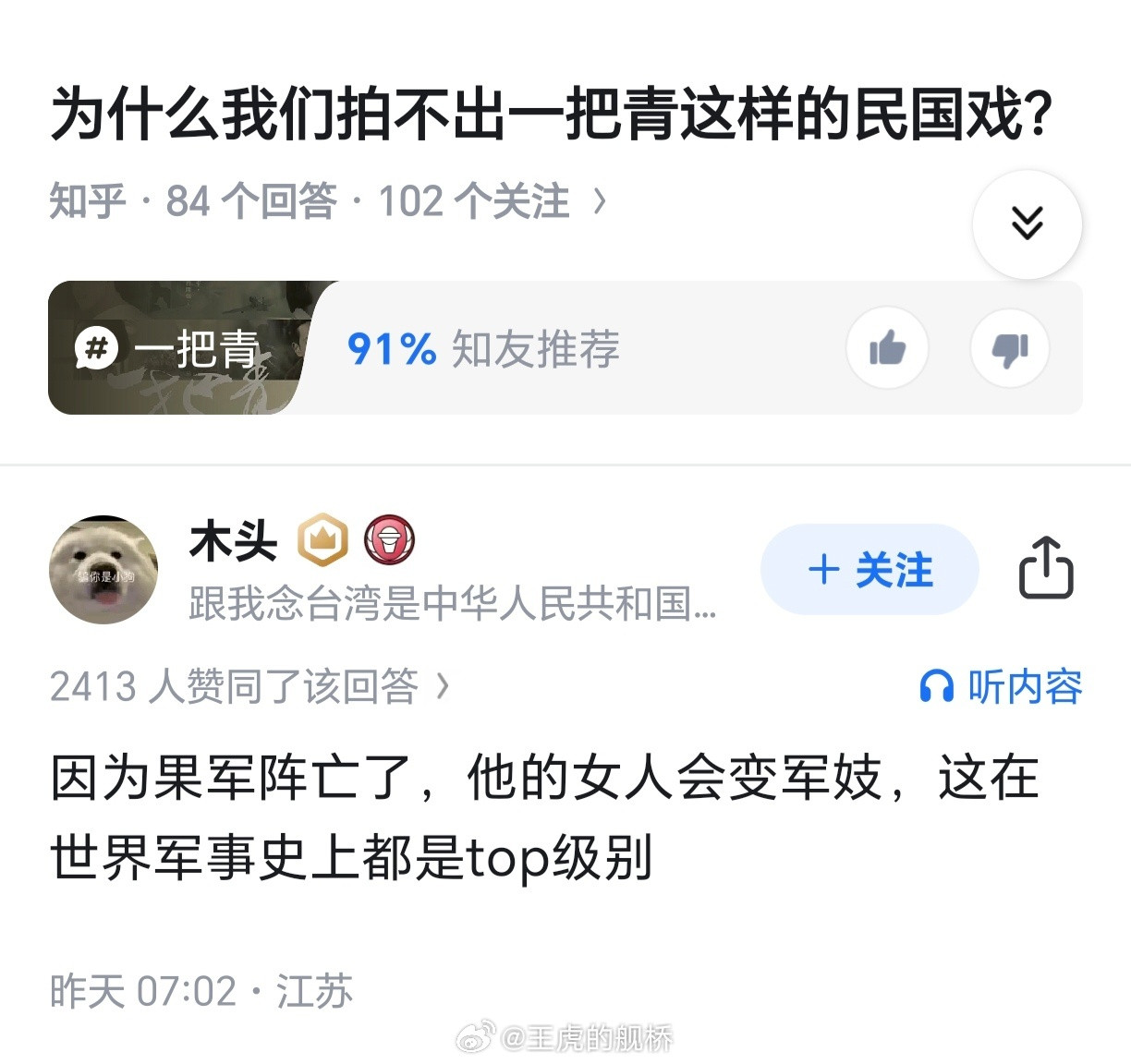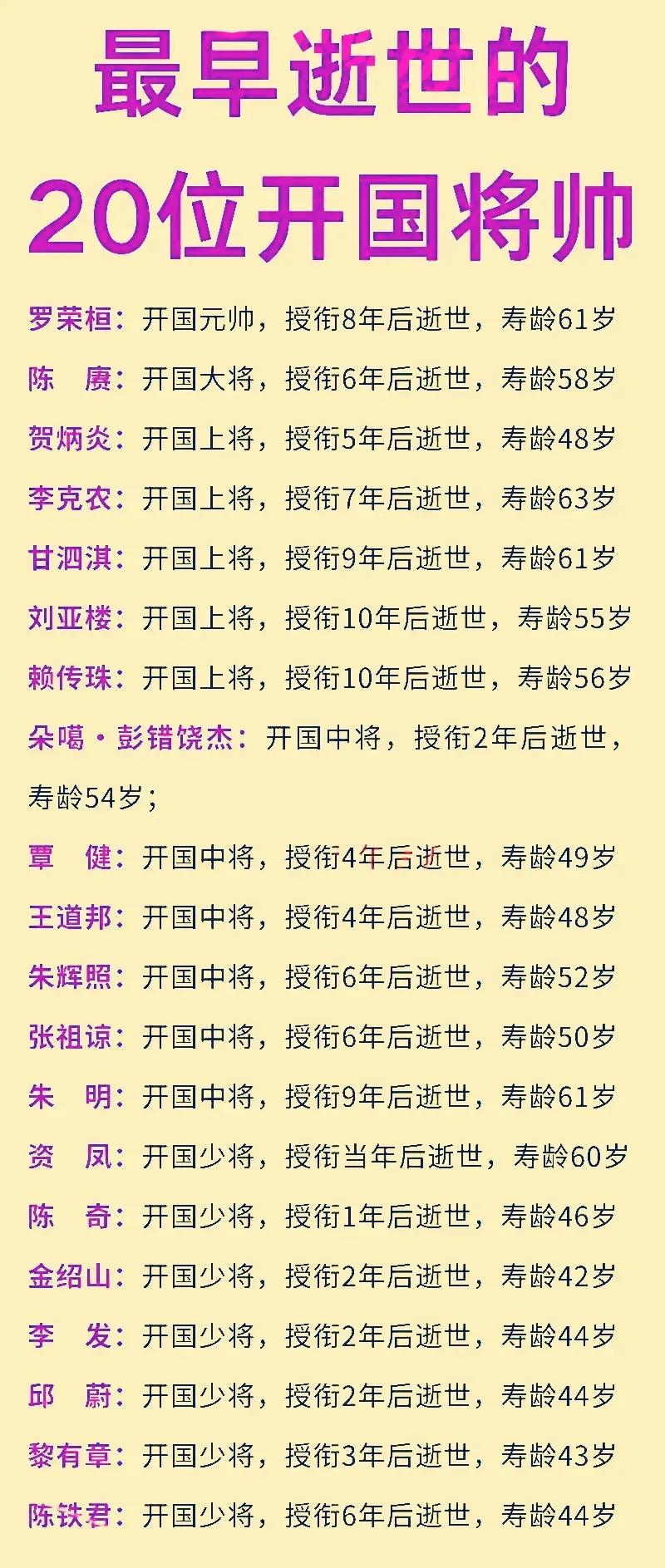705年,一天,武则天还没起床,张柬之突然带兵入宫,杀了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逼武则天禅位。太子李显送武则天离宫时,众人弹冠相庆,姚崇却嚎啕大哭起来。 宫门前的风卷着深秋的凉意,刮在李显脸上时,他刚要抬手抹去嘴角不自觉扬起的笑意,眼角余光就瞥见了跪在地上的姚崇。那哭声实在太扎眼了,像一把钝刀割在满朝文武的欢腾里,连空气都跟着滞涩了几分。 张柬之皱着眉踢了踢姚崇的衣角,“姚大人莫不是哭糊涂了?今日是光复李唐的好日子,该笑才对。”姚崇没抬头,肩膀耸得更厉害,泪水混着朝服上的尘土往下淌,“臣不是哭大唐,是哭天后。”这话一出,周围的喧闹声瞬间矮了半截,连李显脸上的笑都僵住了。 谁都知道姚崇是个聪明人。当年武则天改唐为周,满朝老臣或死或隐,他却凭着一身才干在新朝里步步高升,从地方小官做到了宰相。有人骂他趋炎附势,他从不辩解,只是埋头做事,连武则天都曾笑着说:“姚崇这性子,倒像块捂不热的石头,可偏偏用处最大。” 可此刻这块“石头”,正为一个失了势的女皇帝哭得撕心裂肺。 武则天坐在銮驾里,车帘被风掀起一角,露出她花白的鬓发。她没看跪在地上的姚崇,只是望着宫墙上盘旋的乌鸦,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让他哭吧,这满朝文武,也就他敢为我掉几滴真心泪。”李显站在车旁,手心沁出冷汗,他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也是这样坐在銮驾里,把他护在身后,对着那些虎视眈眈的宗室说:“我儿胆小,你们莫要吓他。” 姚崇的哭声渐渐小了,他扶着地面慢慢起身,朝銮驾的方向深深一拜。那拜礼极重,额头磕在青石板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等他再抬头时,脸上已看不出泪痕,只剩下平日的冷静:“臣失态了,请陛下(指李显)治罪。”张柬之刚要开口斥责,却被李显拦住了。新皇帝望着姚崇,忽然觉得这位大臣眼底藏着的东西,比满朝的欢呼雀跃更让人捉摸不透。 銮驾缓缓驶离宫门,车轮碾过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姚崇站在原地,看着那抹明黄色的身影消失在街角,忽然轻轻叹了口气。旁边的小吏凑过来,压低声音问:“大人,您这又是何苦?张相公他们正等着给您庆功呢。”
姚崇摇摇头,没说话。他想起三天前,武则天把他叫到长生殿,指着满桌的奏章说:“这些事,我以后怕是管不动了。你是个有担当的,李显性子软,你得多帮衬着点。”那时他还以为是老太太随口念叨,如今才明白,那是托孤。 这场“神龙政变”,终究是成了。可姚崇心里清楚,李唐的江山能回来,不全是靠刀光剑影。武则天在位十五年,打击门阀、发展科举,把多少寒门子弟抬进了朝堂?就说眼前这些欢呼的大臣里,有一半都是踩着她铺的路才爬到今天的位置。如今她倒了,众人忙着撇清关系,恨不得把“武周”两个字从史书里抠掉,可那些实实在在的功绩,难道也能跟着抹去? 夜里,姚崇独坐书房,对着一盏孤灯发呆。桌上放着武则天赏赐的那方紫石砚,砚台边缘刻着一行小字:“守正出奇,方为正道。”他忽然想起当年,自己因为弹劾酷吏来俊臣,被武则天贬到亳州,临行前老太太也是把这方砚台塞给他,说:“天下总要有人敢说真话,你去地方历练历练,回来我还用你。” 窗外传来更夫打更的声音,梆子敲了三下,已是三更天。姚崇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三思”两个字。他知道,张柬之这些人眼里,他今天的哭泣是“不识时务”,可他偏要做这个不识时务的人。武则天固然有过错,可她也是个实实在在的帝王,功过是非,总得有人敢在她落难时,替她留几分余地。 后来的事,果然如姚崇所料。李显登基后,朝堂很快陷入混乱。韦后想学武则天临朝称制,安乐公主忙着争权夺利,张柬之等五位功臣被排挤流放,死的死,贬的贬。唯有姚崇,因为当初那一场痛哭,让武则天的旧部觉得他念旧情,也让李显觉得他“憨直可倚”,反而在波诡云谲的朝堂里站稳了脚跟。 有人说姚崇是老狐狸,哭一哭就保住了性命。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天宫门前的眼泪里,一半是为武则天的晚景凄凉,一半是为这摇摇欲坠的大唐。他哭的,是一个女人在权力巅峰的孤独,也是一群臣子在时代洪流里的身不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