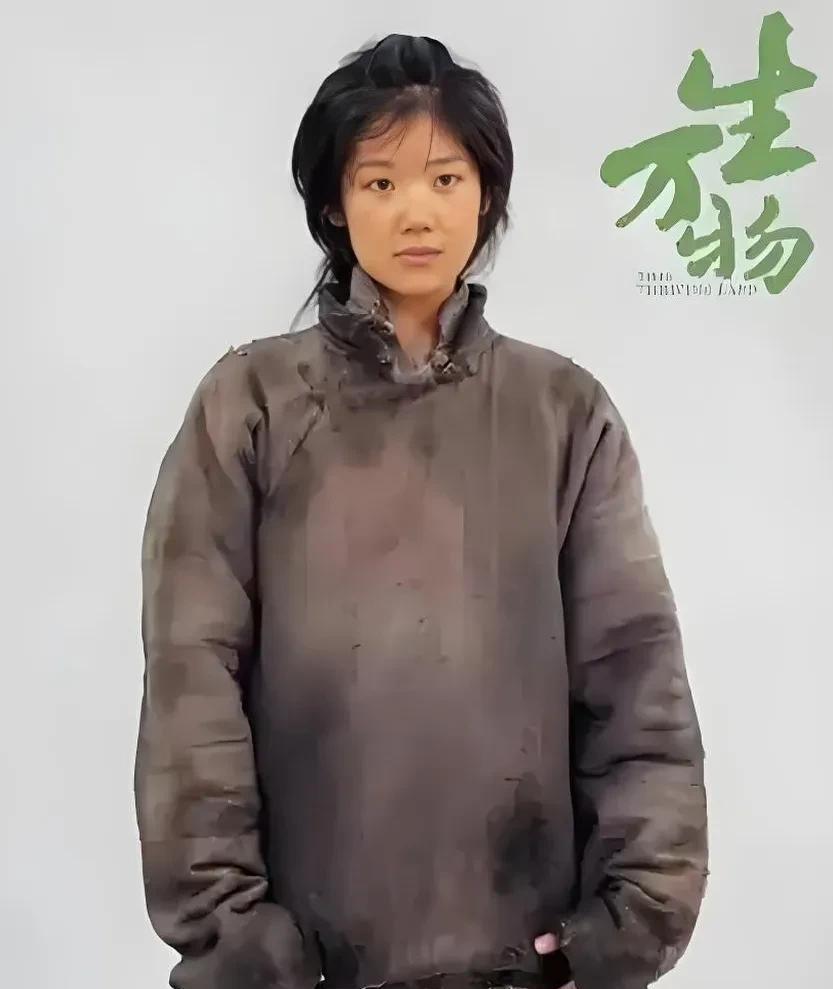1955 年钱学森回国后,发现国内尖端人才严重缺乏,无法承担起当时最关键的装备研发任务。“人才,” 他突然对助手说,“没有人才,再好的蓝图也是废纸。” 说这话时,他刚从东北的军工厂考察回来,车间里的老师傅拿着苏联专家留下的图纸叹气,说 “上面的公式像天书”,而几个大学毕业生对着火箭发动机的草图,连基本的推力计算都无从下手。 窗外的白杨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像在应和他心里的焦虑。 中科院的会议室里,钱学森把一份国外高校的课程表拍在桌上,红笔在 “航空工程”“流体力学” 等专业名称下画了重重的线。 “不能等,” 他对前来座谈的教育专家说,“常规培养周期太长,我们得办一所‘速成班’,直接对接国防需求。” 当时国内的高校还在沿用民国时期的教学体系,理工科多偏重理论,与导弹、原子能等尖端领域脱节。 他想起自己在加州理工学院时,学生能在实验室里亲手组装火箭模型,而国内的学生连风洞是什么模样都没见过。 1958 年的夏天,中关村的一片空地上,工人正用竹竿搭起临时教室。钱学森穿着布鞋,踩着满地的砖头瓦砾,给施工队比划着 “实验室要离教学楼近,学生上完课就能动手实操”。 他亲自拟定的招生简章上,专业设置直白得近乎 “功利”:原子核物理、星际航行、自动化 —— 全是国家最急需的领域。 有人质疑 “这样会不会太急功近利”,他指着操场上正在军训的学生说:“国家等着导弹保家卫国,我们的学生就得带着任务学。” 第一堂课讲 “工程控制论”,钱学森站在黑板前,手里捏着半截粉笔,身后的墙上挂着他从美国带回来的火箭结构图。 台下的学生多是十七八岁的少年,眼睛亮得像星星,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公式,有人连他随口提到的参考书名都抄了下来。 讲到关键处,他突然停下来问:“谁能说说,咱们国家的铁路轨距是多少?这对导弹运输有什么影响?” 课堂瞬间安静,他笑了笑:“搞国防科技,不能只盯着图纸,得知道脚下的土地是什么样。” 中科大的实验室里,总能看到钱学森的身影。有次深夜,他发现几个学生围着一台旧车床发愁 —— 他们想仿制一个火箭燃料喷嘴,却怎么也达不到精度。 他脱下外套,挽起袖子手把手教他们调整转速,铁屑溅到他的衬衫上,烫出几个小洞也没在意。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的,” 他擦着手上的油污说,“你们现在多磨坏几个零件,将来导弹上天就少几分风险。” 那台车床后来被学生们漆成红色,旁边挂了块牌子:“钱先生用过的‘教具’”。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戈壁滩上,1960 年第一枚仿制导弹 “东风一号” 即将发射。 钱学森在指挥车里,看见操作台上有个年轻技术员的动作格外熟练,细问才知是中科大第一届毕业生。 “您在课堂上讲的‘推力矢量控制’,我们在这儿用上了。” 年轻人激动地说,手里的记录本上,还贴着当年听课时抄的板书。 导弹升空的瞬间,尾焰染红了半边天,钱学森想起三年前在中科大的开学典礼上,他对学生们说 “你们是祖国的火箭,要带着梦想起飞”,此刻终于有了回响。 1970 年 4 月,“东方红一号” 卫星成功入轨,测控中心里一片欢腾。负责轨道计算的团队中,有六位是中科大的毕业生,他们用算盘打出的数据,与计算机的结果分毫不差。 钱学森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卫星参数,想起当年在课堂上,他让学生们用最原始的计算尺练习弹道推演,说 “基本功扎实了,将来用什么工具都不怕”。 窗外的玉兰花正开得灿烂,像极了那些年在中科大校园里,学生们夹在课本里的花瓣标本。 晚年的钱学森坐在轮椅上,翻看中科大的校史,指着一张老照片笑了 —— 那是 1958 年的开学典礼,他站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身后是还没完工的教学楼,学生们坐在小马扎上,听得一脸专注。 照片的背面,有他当年写的一行小字:“人才是种子,只要给足阳光雨露,就能长成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