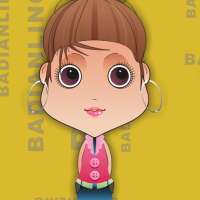烈士江姐儿子定居美国,记者问他为何不回国?他的回答很现实 1949年重庆渣滓洞的牢房里,空气里飘着潮湿的霉味。 那个季节,山城的湿气总是钻进骨头缝里。牢房的角落里,一个年轻女人俯身在地,她手里拿着一根竹筷,是她早些时候偷偷藏起来的。 她把筷子一端磨尖,扯了些棉絮烧成灰,兑水调成墨。 用尽全身的力气,一笔一划地写下了几行字。这封信里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什么英雄豪言,有的只是对孩子的深切牵挂和一个母亲最后的安排。 她说,如果她不幸没能活下来,就把孩子“云儿”托付给那位叫“幺姐”的人,还说,希望他长大以后能走父母的路,为新中国出一份力。 说这话的时候,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明天,但她很清楚,信得交出去,人也就安稳了。 那个女人就是江竹筠,人们后来说她是江姐。 再后来,有人写了《红岩》,又拍了电影《烈火中永生》,江姐变成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心里的烈士代表。但在那个牢房里,她不是符号,也不是象征,她只是一个即将与这个世界告别的母亲,一个还惦记着儿子穿不穿得暖、吃不吃得饱的人。 她的丈夫彭咏梧已经牺牲了,亲人也大多失联了。 她唯一能想到、也唯一能相信的那个人,其实她从未谋面。那人是彭咏梧的前妻,叫谭政姴。 江姐在信里称她“幺姐”。一个女人把自己孩子托付给另一个女人,还是前夫的前妻,这种信任不是感情冲动,而是身处绝境时对人性最根本的判断。 信最终送到了谭政姴手中。 她看完后没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把彭云接回了家,还改了自己的名字叫谭正伦。 从那天起,她多了一个儿子,也多了一份从未许下却必须承担的责任。 那几年,他们搬了很多次家,为的是避开可能的盯梢和清算。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暗线没那么快清理干净。作为烈士遗孤的抚养者,谭正伦带着孩子几乎是在夹缝中生活。 彭云就这样一路被养大。 1965年,他成了四川的高考状元,考进了哈军工。 那时候的哈军工,不是一般人能进的地方,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军工科技摇篮。 大学毕业后他去了沈阳的一个军工单位工作。 后来改革开放了,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招生。他又考进中科院的计算所,继续往深里钻。当时中国的软件领域还几乎是空白,谁要是能在这方面搞出点东西,那就是开荒者。 也是在这段时间,他拿到了国家公派留学的名额,去了美国。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第一批送出去的年轻人。 他到了美国之后,一头扎进了人工智能的研究,博士论文还被美国的出版社看中,邀请他出书。 这对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学者来说,是一种极高的认可。随后他便进入马里兰大学,成为了计算机系的终身教授。 但也就在这段时间,一些质疑的声音冒了出来。 有人说,他这么有本事,怎么不回来?江姐当年拼了命写信说要孩子“以建设新中国为志”,结果这孩子倒好,在国外安了家,连国籍都换了?还有人说,他是不是已经加入了美国籍,这些年来怎么就没见他回来工作? 面对这些声音,彭云没有回避。 他接受采访时说,他从来没有、也不会加入美国国籍。 他说,他知道自己是烈士的孩子,他一直记得母亲在信里写的那几句话。他没忘,也不敢忘。 至于没回国这件事,他也说得很实在。 当年出国是为了学习,是为了研究。他想着,等哪天有了成果,能拿得出手了,就回来报效国家。 但现实是,他的研究方向太前沿,不是三年五载就能见成果的。 而等到他意识到自己的年纪大了、机会少了的时候,留在美国已成常态,身子和工作都扎在了那里,再回来也不现实了。 他说,他知道这让很多人失望了,也确实觉得愧对母亲的遗愿。 但他也没有躲着不讲,只是反复说了一句:“我始终是中国人。”这是他的坚持,也是他给所有质疑一个最直接的回答。 1999年,江姐牺牲五十周年前夕,彭云带着妻子和儿子彭壮壮回到了四川。 那天他们一家三口去一家小饭馆吃饭,老板的母亲听说来了江姐的后人,激动得不行,拉着彭壮壮讲了好多她年轻时听过的烈士故事。彭壮壮一边听,一边点头,哪怕这些他小时候已经听过无数遍。 他没打断老奶奶,只是很认真地听完每一句。 那天走的时候,饭钱老板不肯收,还非要送他们一包自家腌的腊肉。 彭壮壮接过那包腊肉,心里那点被压着的情绪一下子就翻上来了。他说,那一刻,他忽然特别清楚地知道,自己以后要干嘛了。 那年他还在普林斯顿读数学博士。 周围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一群人,毕业之后去硅谷、去投行、去高校,哪一条路都前程似锦。 但他想了又想,还是决定回国。 他不觉得自己在做牺牲,也不觉得回国是为了“完成祖母的遗愿”这么重的话。 他只是觉得,那封写在牢房地上的信,该有人接着往下走。 博士毕业后,他真的回到了北京。 有人劝他留在国外,有的是高薪职位,有的是研究自由。 他都谢绝了。 他在国内高校任教,写论文、带学生,也继续自己的研究。他说,这是他能为这个家、为这个名字做的事。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