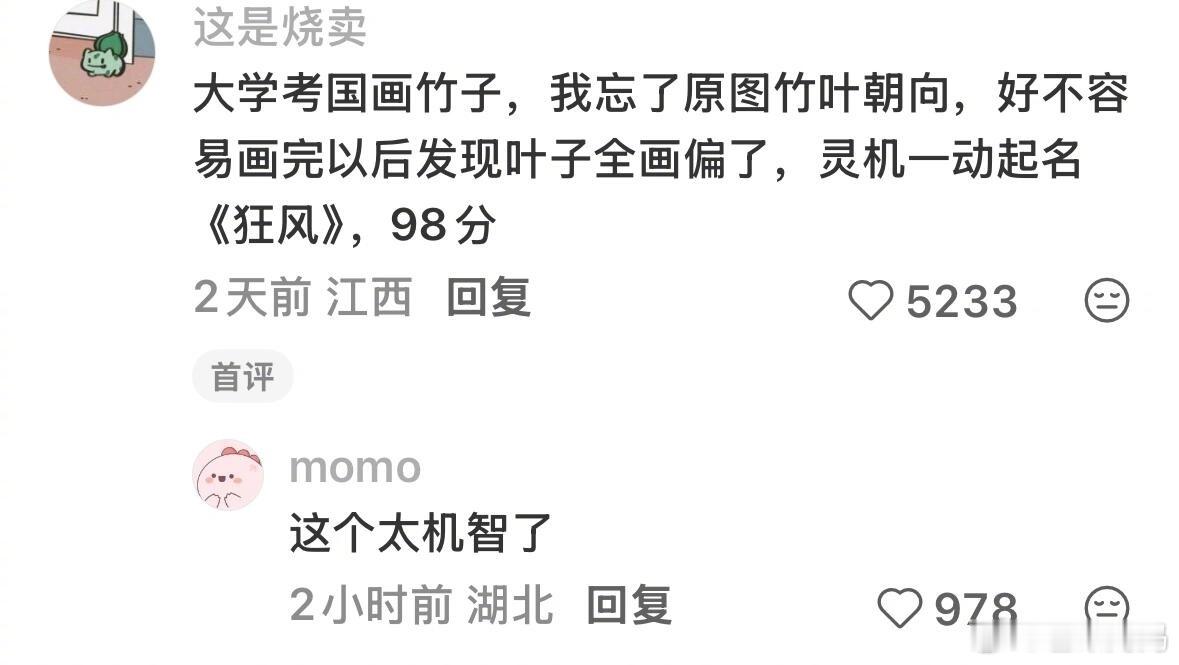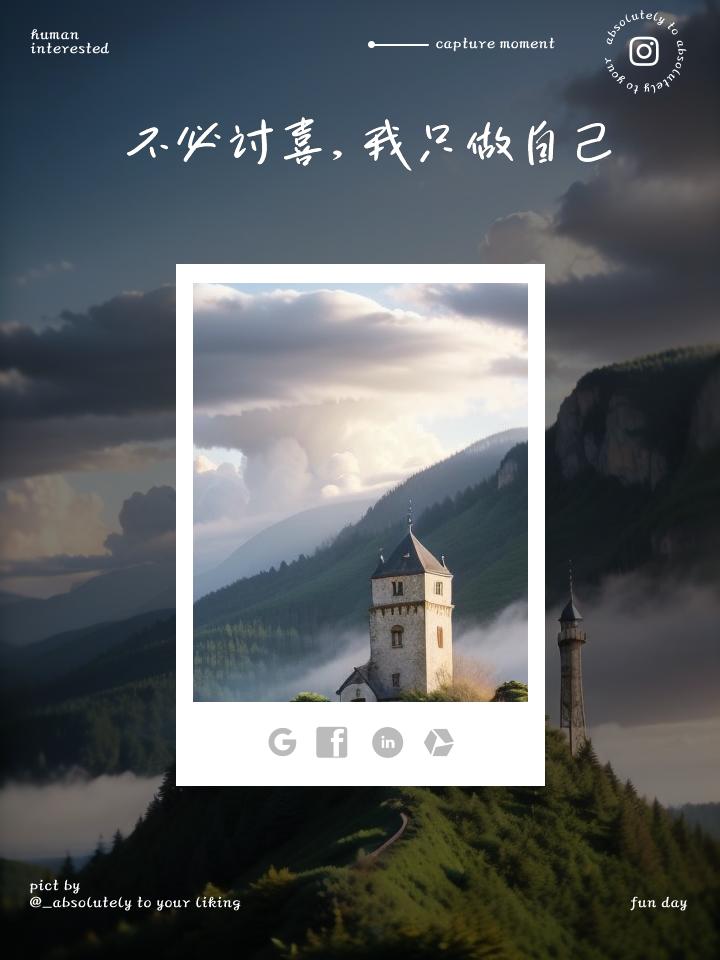“早知道做人这么累,下辈子再也不做人了。” 这句话,很多人或许都在某个时刻暗暗想过,甚至脱口而出。也许是因为一段让人心力交瘁的感情,也许是被生活里的柴米油盐压得喘不过气,又或者,仅仅是为了一双孩子想要的、几百块的足球鞋。在那些瞬间,人总觉得这世上做什么都容易,哪怕做一条流浪狗,似乎都比做人轻松——做什么都好,就是别再做人。 那么,我们真的能摆脱这种“心累”的一生吗? 答案是:不能。 戴维·迈尔斯在《社会心理学》中提出:当我们开始扮演一个新角色,其实也就开启了一场自我觉察的旅程。我们逐渐被这个角色所内化、所塑造,最终活成了它的样子。 人与其他生命的不同或许正在于此。一株植物、一只动物,一生只扮演一个角色;而人,却总被贴上各种各样的身份标签——你是父亲,也是儿子;是伴侣,也可能曾是别人婚姻之外的影子;你是一名员工,一个朋友,甚至某个陌生人眼中值得信赖的倾听者……每一个身份,都对应着一套看不见的“行为规范”。就像老话说的:你是什么人,就得干什么事。 而光是这些角色中随便挑一个,就足够人忙活一辈子了。 于是有人想:既然这么累,那我就不结婚了。我无法选择“前半生的我”,但“后半生的我”总可以自己决定吧?不结婚,就不用承担丈夫或父亲的责任,生活不就轻松多了吗?心情,或许也会因此明亮起来。这大概也是当下越来越多人选择不婚的原因。 可这样的选择,到底是对是错? 没人能给出标准答案。就像你今天做的一件好事,也许很多年后才结出善果;你某次不经意的错误,也可能在遥远的未来带来回响。一切都需要时间来验证。 而我,却持一种不太一样的看法。 我认为,人还是应当尽量去结婚、去走入关系,但不必把每一个角色都扮演得尽善尽美。我们可以放低要求,对彼此减少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让每个身份的负担轻一点、再轻一点。 生活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不一定要在“全得”与“全舍”之间做决断。我们也可以对“少一点拥有”感到满足,对“能接受的失去”坦然放手。若能如此,我们既不会像无欲无求的树木那样活得空洞,又能留下那些真正令我们愉快的角色。 这样,不也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