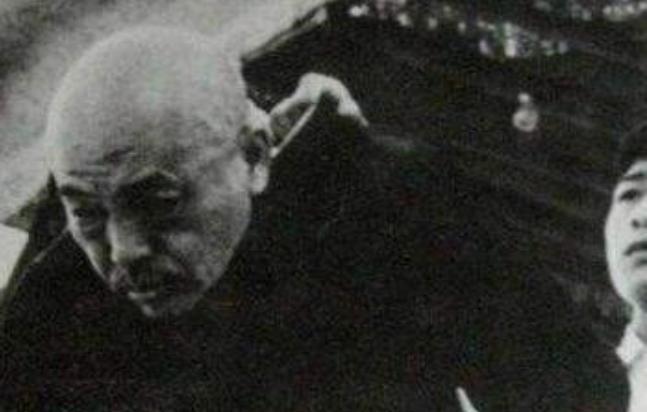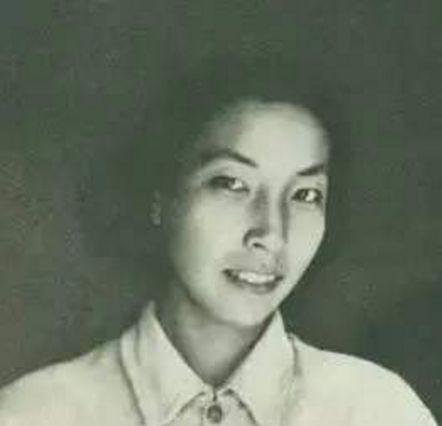1991年,彭德怀曾经的妻子浦安修在临终前给杨尚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恳切地请求道:“杨尚昆同志,求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查看彭老总的传记……”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91年,在北京的病房里,浦安修已是弥留之际,她非常瘦弱,连呼吸都显得费力,却怎么也不肯合眼,她似乎在等一个人,或者说,一个承诺。 当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走进病房时,她用尽全身力气,吐出几个字:“尚昆同志,请求您亲自审查彭老总的传记” 这份临终托付的背后,是一段纠缠了几十年的悔恨、守护与承诺,而故事,要从那半个梨说起。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的命运急转直下,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样砸在了他的妻子浦安修身上。 当时浦安修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却一进校门就被拦下“谈话”,没完没了的“思想调查”和“攻心”谈话,持续了三十七天,几乎把她的精神压垮。 终于,一个深夜,她回到吴家花园的住所,彭德怀没说什么,正借着灯光给侄孙缝补一个破了的书包,手指被针扎出了血珠子,这一刻,浦安修再也绷不住了,哭着说:“我们离婚吧。” 老元帅沉默了许久,拿起一个梨,默默削好,切成两半,递给她一半,轻声说:“你要想好了,真要离,就吃了它。” 浦安修颤抖着手接过,流着泪把那半块梨咽了下去,“分梨”,即“分离”,这一口,成了她余生都无法原谅自己的痛。 谁能想到,二十一年前,在太行山,他们也是这样开始的,那时的彭德怀已年过四十,是战功赫赫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却因表妹“周瑞莲”为反抗包办婚姻跳崖自尽、发妻“刘坤模”在战乱中失散改嫁而心灰意冷。 可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在“陈赓”的“设计”下,他在排球场边见到了二十岁的北师大女生浦安修。 面对这位扎着马尾辫、充满活力的姑娘,彭德怀坦白了自己的年龄、草根出身和失败的婚姻,浦安修却仰头看着他,眼里全是崇拜:“我读过报道,您在太行山帮老乡修屋顶,啃着硬馍,我敬佩的就是您这样的英雄!” 而这份敬佩,超越了年龄和身份的差距,那年冬天,太行山司令部简陋的土坯房里,多了一对印着喜鹊的红瓷杯,也多了一位女主人。 可这份温情,终究没能扛过历史的狂风,分梨之后,吴家花园再无女主人,只有侄女“彭梅魁”照顾着元帅的晚年。 直到1974年,彭德怀病危,癌细胞已全身扩散,弥留之际,他神志不清地念叨着:“安修胃寒,别让她吃生梨。” 四年后,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浦安修抚摸着覆盖党旗的骨灰盒,哭得几近昏厥,她对老友“杨献珍”泣不成声:“我真傻,那年分梨,我应该把刀扔了的,我最不该在他最痛苦的时候离开,最不该连最后一面都不去见。 这份悔恨,化作了她此后十年的全部动力,她要为丈夫立传,完成一份迟来的救赎。 国家补发的四千八百元,她一部分捐给彭德怀老家的学校,一部分送给当年的警卫员结婚用,剩下的四千块压在枕下,成了她写书的启动资金。 她拖着病体跑遍全国,在江西找到炊事班长的后人追忆往事,在石家庄档案馆一头扎进去抄录了三天三夜的会议记录。 有一次在八达岭不慎摔进山沟,被人救起时,怀里还死死抱着彭德怀1938年的行军笔记。 浦安修以彭德怀写下的八万字“交代材料”为基础,补充了无数细节,最终整理出整整二十七本厚厚的硬皮手稿。 这便是1991年,浦安修在病榻上托付给杨尚昆的那份沉甸甸的书稿。 杨尚昆接过书稿,湿了眼眶,他想起四十多年前,自己初到太行山,彭德怀还瞧不上他这个“学院派”,谁知九年并肩作战下来,两人成了过命的交情。 湘江血战后,他们挤在草棚里分食半块烤红薯,庐山会议后,他常去吴家花园探望,总看到老战友一个人蹲在池塘边发呆,这份情谊,让他深知这份托付有多重。 “放心,我一定认真看!”杨尚昆郑重承诺,尽管当时主政广东,日理万机,他还是推掉了下个月的所有会议,夜以继日地审读这二十七本手稿。 几个月后,他拍案叫好:“这书,一打开就放不下!”只可惜,浦安修没能听到这句赞扬,她在托付书稿的五天后,就平静地离世了。 为了不负所托,杨尚昆在书稿付印那年,还特地去印刷厂盯着封面烫金,当《彭德怀自述》这个书名在机器下被压出清晰的凹痕时,他仿佛触摸到了太行山那些永不冷却的番号。 直到1998年,《彭德怀自述》正式出版,读者终于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彭德怀,从平江起义的硝烟,到朝鲜战场的炮火;从为民请命的万言书,到身陷囹圄也挺直的脊梁。 书出版那天,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带着这本还散发着墨香的新书,来到浦安修的墓前,轻轻地将书放在墓碑旁。 这份跨越了生死的约定,终于完成,而被尘封的历史,也在这本书里,重新见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