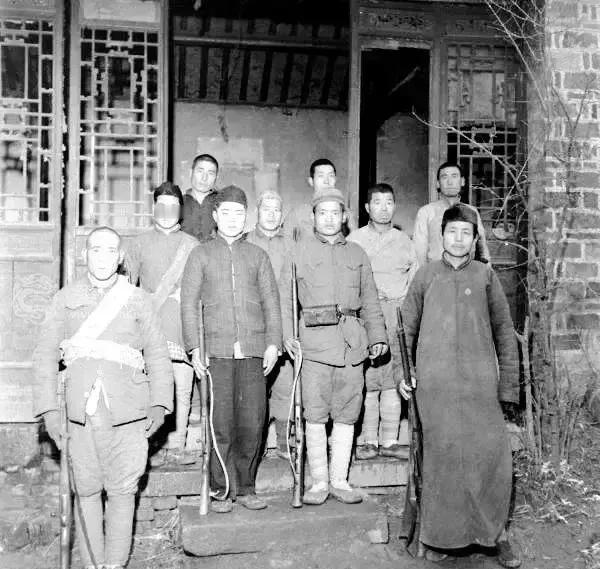1947年,一个地主偷偷放走了地下党员,但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找他算账时,地主却说:“你知道我弟弟是谁吗?你敢动我一下试试!”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7年,江淮水系以南的乡镇还未从战火中缓过神来,那一年,战线紧绷,街头巷尾流传着关于内战的风声。 扬州西郊的谷南村,一座老宅院隐藏在青瓦白墙间,屋前有一株老槐树,枝干粗壮,像经历过许多年头似的,那座宅院的主人姓郭,名瑞生,是村中最有家底的地主之一。 郭家的地多,打小不愁吃穿,郭瑞生不像其他人家那样高高在上,他出入时总带着点书卷气,待人不急不慢,讲话也总压着声儿,说得少,但听得人信。 他年轻时在扬州念过两年私塾,识得字,也看过不少旧书,对朝代更迭的风浪并不陌生,他从不参与什么政治组织,更不热衷于村务,只希望安稳过日子。 但这一年不太平,村外山路多了陌生人,枪响时常传来,穿着草绿色制服的人一拨拨路过村头,背后总押着人,披头散发,衣不遮体,人们开始躲进屋子里,夜里听风吹过墙头,也不敢点灯。 郭瑞生有次从田头回来,远远看见一队人押着一个血迹斑斑的年轻人经过村口,那人低着头,身子被打得直不起来,步子沉重,似乎随时都能倒下,村里人认得他,是前些年在镇上教课的朱姓教师。 朱先生来谷南村时,带着几本发黄的书和一包布衣,他常在晚饭后到村口晒月光,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和人讲些远方的事,他没说过自己是谁,也从不提背景,只是说人活一口气,不能全靠命。 他离开时谁也没送,大家只记得他临走那天站在村口,望着西边的天说了一句像是在告别的话,郭瑞生记得他,也记得那天雨下得极大,他的堂弟躲雨时曾被朱先生拉了一把。 见他如今成了俘虏,郭瑞生心里翻腾,这不是谁家的仇家,也不是自己地里闹事的佃户,他只是个曾讲过“人要有骨气”的先生,一个曾在祠堂里讲解过《孟子》的人。 那天傍晚,郭瑞生走过村西头的柴垛,突然停住了,他闻到空气中不属于这个季节的气味,那是血与尘混合的味道,他顺着土路慢慢走,转过一堵墙角,看见两个士兵守着一扇铁锁的木门,里面隐约有动静。 郭瑞生没立即靠近,他回家后,独自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一直没有开灯,夜深了,他起身取出几样东西,装进旧布包,出了门,月光将院落照得雪亮,他穿过后巷,一路避着人,靠近了那处木门。 两个士兵昏昏欲睡,他将包裹轻放在地上,悄悄解开锁,门开了一道缝,里面是瘦弱的人影和一双明亮却带血的眼,郭瑞生未多停留,转身从侧门离开,只留一行鞋印印在潮湿的泥地里。 第二天清晨,天还未亮,村里就炸了锅,赵姓队长带人挨家搜查,一队人马站到了郭家门前,他没有惊慌,只是叫人煮水、添茶,待客之礼一样不少。 他并未开口争辩,也未表示反抗,静静站在门槛边听着外头的脚步乱响,当那一群人走进来质问时,他抬头,脸色平静如常,说了一句话、 语调不高,却像一道石子落入静水,让人不敢靠前一步,气氛顿时凝固,那些人彼此望着,竟无人敢先动手。 这场风波就这样散了,赵队长并未留下任何纸条或凭据,只是瞪了一眼便匆匆离开,他走得快,像是怕晚一步就要掉入陷阱。 村里人议论纷纷,有人说郭家在省里有人,有人说郭瑞生是“会变”的人,郭瑞生回到屋里,照旧饮茶,只是那壶水,从头到尾没续过第二次。 数月后,政权更迭,风向突变,村里开了会,说要清算旧账,郭瑞生的名字也出现在名单上,审查小组到村里,郭家院外站了不少人,有看热闹的,也有愤怒难言的老佃户。 正当局势不明时,一纸公函送至村部,上有一行署名,写着一个久未出现的名字,那纸信里写明郭瑞生在动乱时期救过重要同志,字迹端正,情理俱在,之后还有人作证,说朱先生确实因他之助才得以脱身。 这件事在村中传了许多年,有人说他是借机自保,也有人说他是赌了一把未来的棋,可更多人说,那不是赌,是他这一生唯一一次选择站到他人前面,不为地,不为田,只是为了一点情,一份念。 多年后,郭家的屋檐依旧挂着风铃,每逢春风起,铃声悠悠,村口的老槐树下立了一块小石碑,没有字,只刻着几道深浅不一的纹路,据说那是朱先生来访时留下的痕迹。 他没有久留,只是站了站,看了看,点了点头,然后转身离去,郭瑞生站在门口,目送他离去,像当年朱先生第一次离开谷南村那样,没有言语,只余一地落叶。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息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隐蔽战线英雄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