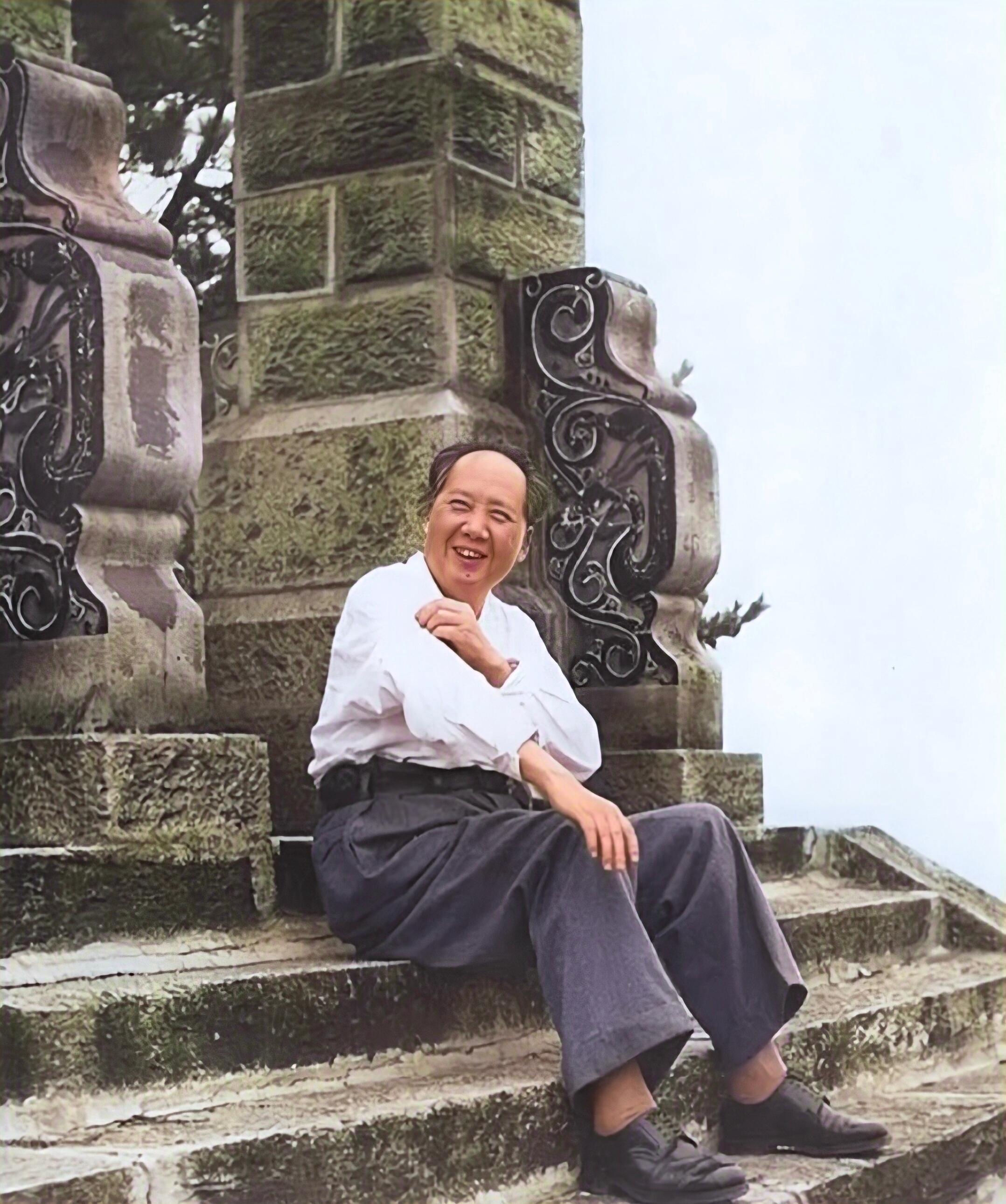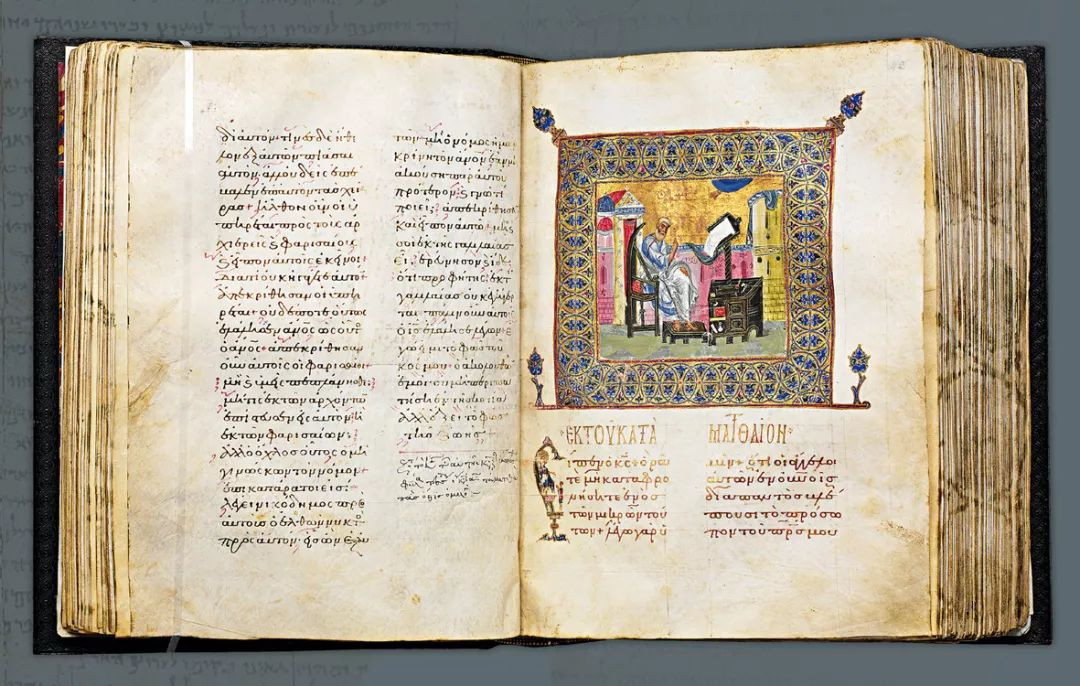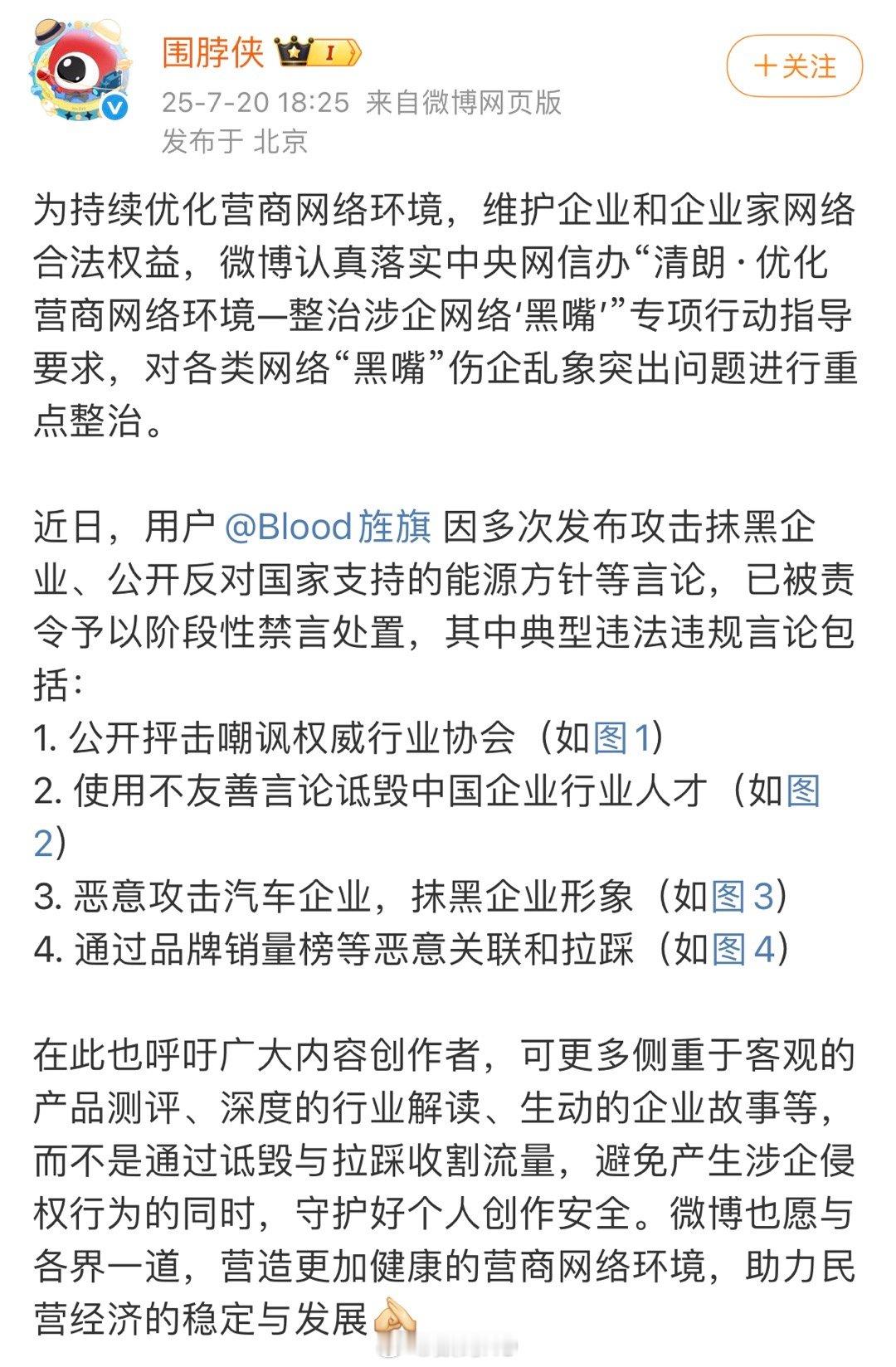这些年呢,关于满清皇帝到底是“通古斯大酋长”还是“中国皇帝”,明粉清粉在小圈子里吵得还挺激烈的。
不过有一说一,这种大多数时候都在空对空的“定性分析”,其实只是双方在借机发泄而已,很难说有什么营养。而且很明显,整个清政权也好,各位满清皇帝也好,在其两百多年的历史中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这种时候,我们不妨来点“定量分析”,看看不同满清皇帝在类似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来略微探究一下他们在自己到底是“通古斯大酋长”还是“中国皇帝”这个问题上的自我认知。
至于样本,康雍乾三朝很明显比较有代表性,鉴于写了《大义觉迷录》的实心眼雍正在这类问题上的观点众所周知,我们就来看一看康麻子和他的好圣孙的观点差别吧。
关于如何看待汉人和满汉差异,康麻子是这样的:
“華亭張文敏公照,年十八捷南宮,臚傳後引見,未奉欽點,先仰奏云:「臣張照年幼,未嫻吏治,懇恩教習,願讀中秘書。」帶領官掖之不起。聖祖顧左右曰:「小蠻童乃頗有膽。」”
称汉人为“南蛮”,堂堂一甲进士引见时因为年轻,康熙竟然当面叫人“小蛮童”;
“上谕大学士等曰:柔远能迩之道汉人全不理会,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蒙古终年无杀伤人命之事,即此可见风俗醇厚。若直隶各省,人命案件不止千百,固縁人多亦习尚浇漓使然也。”
在上谕中明确把蒙古人当自己人,把汉人描述为某种残忍排外的野蛮民族;
“许三礼参徐乾学荐举熊赐履,往者皆言熊赐履不好,今见朕起用熊,又言熊赐履好,熊赐履所作《日讲四书解义》甚佳,汤斌又谓不然。以此观之,汉人行径殊为可耻。”
专门将理学名臣之间的倾轧总结为“汉人行径”;
“谕议政大臣大学士、九卿等、天下承平日久、汉官但能作无实之文、说现成话。至军务大事、并不能尽职。平日常谓旗员赴任、多挈人口、骚扰地方。汉官家口少、所需无几。朕因此曾屡向汉大臣言、汉官不能骑马耐劳。设有紧急之事、边塞地方、必兼用旗员、方有裨益。汉官或自谓清廉、不取不与、节用度日。如解马运粮等事、督抚俱差州县汉官。汉人出口、一二仆从、何济于用。遇劳苦之处、旋亦逃亡、纵令参处何益。”
到了这里,不光是看不起汉官,甚至于把一部分汉官的清廉行为都作为缺点进行批判了。
所以说,康熙确实全无多民族普世帝国统治者的自觉,相比于中国皇帝,妥妥的更像是一个通古斯大酋长。
反过来说,康麻子的好圣孙,知名人形马基雅维利主义结晶乾隆,又是怎么看待这类事情的呢?简单举两个例子:
“自定鼎以來,八旗、蒙古各有寧居,祖宗墟墓,悉隸鄉土,喪葬可依古以盡禮。而流俗不察,或仍用火化,此狃於沿習之舊,而不思當年所以不得已而出此之故也。嗣後除遠鄉貧人,不能扶柩回里,不得已攜骨歸葬者,姑聽不禁外,其餘一概不許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
火葬是满洲恶习,当年祖宗搞这个都是太穷了被逼的,现在不许再搞了,否则要判刑。
“我满洲过于汉人者惟在风俗淳厚,失此又何以称为满洲? ”
满人唯一比汉人强的地方就是(对上头)老实,如果人不老实就彻底废了。
这其中体现出来的,和他爷爷康麻子的心态差异,就很明显了。
至于在如何看待“读书人”这件事情上,两者的态度就更可玩味了。
康熙是这么说的:
“张伯行由进士历任按察使、不可以书生待之。”
这汉人不错,可不能再叫人书生了。
“书生辈但知讥评往事,前代帝王虽无过失,亦必刻意指摘,论列长短,无一人为帝王公言。”
书生都是废物,天天闲得没事干就骂皇帝。
而到了乾隆这里,态度可谓是一转攻势:
“朕阅督抚参奏属员及题请改教本章,每有‘书生不能胜任’及‘书气未除’等语。若以书生为戒,朕自幼读书宫中,讲诵二十年,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王大臣为朕所倚任,朝夕左右者亦皆书生也。”
你骂谁书生呢?朕是书生,诸位满洲亲贵也是书生!
而对于华夏的一些传统观念,康熙和乾隆所持的观点不说是完全相反吧,至少也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乾隆搞《贰臣传》,以及修《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给明末诸位忠臣上谥号、给政治待遇这件事,大家应该都知道,细节就不赘述了。
单从个人行为来看,乾隆搞完《贰臣传》后还跑去了宁远,在祖家牌坊上写诗嘲讽:
“若非华表留名姓,谁识元戎事两朝?”
乾隆高强度推崇岳飞,而且不光推崇岳飞,还公开赞同岳飞北伐恢复中原的理念,公开说岳飞就是应该出兵打女真人,赵构是个傻逼和废物,所以说岳全传算是当时的政治正确了。
而相反,康麻子就是赵构粉,从康熙到雍正,满清皇室的主流思想还是,“我们是根基不稳的外来政权,不能激起汉人的民族感情,要鼓励投降派。”
康熙的《宋高宗父母之仇终身不雪论》里面就写到,“若论李纲之忠言不听,岳飞之丹诚不用,设使谏行言听,则必胜金兵于朱仙,生还二帝于汴京,朕实不信也。”
意思是你觉得听了李纲和岳飞的就一定能行?反正我是不信。
而回过头来,乾隆就把他爷爷的脸给打了,在《岳武穆论》里头这么评价赵构:
“及即位之后,当卧薪尝胆,思报父兄之仇。而信用汪、黄,贬黜李纲,不复以河北、中原为念,岂非高宗庸懦、用人不察之过哉?”
康熙这个本质上的通古斯大酋长,很多时候得到西方的高度评价,很大程度上恰好是因为康熙有“民族主义”心态,更像近代民族国家君主,认为满族是优等民族,蒙古人是荣誉满人,其他民族是二等以下公民。
这种心态,和诸多19世纪欧陆民族国家的君主,非常相似。
而他的孙子乾隆,则是一个典型的普世帝国统治者,只认宣称不认人。乾隆认为自己在大清有完美的正统性,大清在中华体系上又有完美的正统性“得国最正”,所以外国君主都要承认他大皇帝的权威,否则就是僭越。
这么稍微盘了一下,不同满清皇帝之间的心态和自我认知变化,是不是稍微清楚了一些呢?[开学季]